從鳥獸草木探源中華古老文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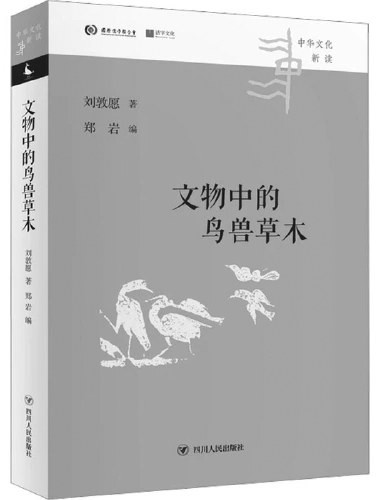
出沒于古代器物與畫像中的鳥獸草木,題材廣泛,映現著人們與自然界生物豐富密切的關聯,以及由此形成的文化含義和藝術脈絡。《文物中的鳥獸草木》一書通過描述這些圖案、紋樣的風格,剖析其意涵,來推想古人對自然資源的認識、改造與利用,復原彼時的生態環境與社會生活,追蹤古族的征伐與遷徙,再現悠遠的宗教禮儀與信仰,呈現出考古材料多方面的價值。
《文物中的鳥獸草木》(四川人民出版社)是從劉敦愿先生生前文稿中編輯而來的一本小冊子。劉敦愿(1918-1997),湖北漢陽人。山東大學歷史系、中文系教授。著名歷史學家、考古學家、美術史學家。1939-1944年就讀于國立藝術專科學校西畫科,畢業后曾在四川省圖書館等單位工作。1947年應聘于山東大學,先后在中文系、歷史系執教。早年致力于山東地區田野考古調查,對建立山東早期考古學文化序列有重要貢獻。晚年專注于美術考古研究,針對史前陶器藝術、商周青銅藝術、東周與漢代繪畫藝術等問題撰寫了一系列論文,在學術界產生了重要影響。著有《劉敦愿文集》。
初識劉先生的研究還要從他那本《美術考古與古代文明》說起,這部著作是他幾十年來對中國古代美術史和考古學研究的成果總結,直到現在仍然是美術考古學專業研究的重要參考書目。在這部著作中,劉先生特別關注到了各種出土文物中的動植物造型和紋飾,尤其是書中有一章“青銅器裝飾紋樣的起源與母題研究”集中討論了各種青銅器中的動物造型和紋樣,這不僅將中國美術史的研究范圍拓展到先秦時代,也對當代人了解早期人類對自然的觀察和應用大有裨益。不曾想在這部著作絕版多年之后,仍有有心人關注到劉先生的這一學術志趣,將他對出土文物中動植物元素的研究整理集結為眼前這本《文物中的鳥獸草木》。這部著作是一本讓人充滿驚喜的作品,它通過解密出土古物承載的動植物元素,讓人們重新回到那個久遠時代里,體味人與自然的互動。
長久以來考古研究更多傾向于通過遺址形制和出土文物來探討當時人類族群的政治制度、宗教、軍事等社會現象,而研究者對出土文物的自然元素關注并不多,它們最多只是以背景的形式輔助上述研究。但越是追溯到人類文明的初期,人類與自然的接觸就越密切,從最初的游獵采集到之后的農耕畜牧,早期的人類無時無刻不在自然中勞作生息,在這一過程中必然會將對自然的觀察和實踐總結為豐富的博物學知識。這些知識一方面是口口相傳的實用技術,之后又以文字形式保存流傳;另一方面這些對自然的觀察以圖像形式留存在了人工物品中,這些圖像或是記錄了人與自然的互動過程(比如巖畫中的狩獵采集),或是將動植物形象圖騰化,展現出人類對自然某方面的崇拜(比如各種器物上圖案化的動物形象),再后來自然純粹成為一種審美元素被裝飾在各類人工器物乃至描繪在畫卷之上。
描繪在畫卷上的動植物在唐宋以后逐漸形成了專門的花鳥畫科,存世較多且得到了充分的研究,但是唐宋之前存世畫卷較為稀少,對動植物的描繪更是鳳毛麟角,對這一時期動植物的形象研究就需要借助各類出土文物的幫助。不過傳統金石學和現代考古學并沒有過多地關注這一研究面向,而較早對中國古代文物中動植物元素感興趣的是英國博物學 家蘇柯仁(Arthur de Carle Sowerby),他于1940年在美國出版了《中國藝術中的自然》(Na?ture in Chinese Art)一書,初步地探究了中國傳統藝術品中呈現的各種自然元素,其中有許多涉及先秦兩漢時期青銅器和陶器動物造型的討論。在這本書出版之后不久,劉敦愿先生也開啟了自己對古器物的考古研究,與蘇柯仁側重采用西方博物學視角審視這些古器物不同的是,劉先生以博物學鑒別為基礎,之后通過綜合運用文獻、考古、藝術、民俗、地理等眾多學科知識來推斷這些動植物形象背后隱藏的文化含義。由于先秦相關文獻的缺乏,直接研究此時期出土文物會面臨諸多困難,劉先生通過上述方法的綜合運用時常會得出頗有見地的觀點,即便如此,他總會謙虛地強調自己的觀點還需要日后通過新出土的材料加以檢驗。
《文物中的鳥獸草木》收錄的文章由編者分為四卷,分別代表了劉敦愿先生對這一類主題的四個研究方向。第一卷側重于說明動植物形象在古器物上的藝術表現。早期古人受限于繪畫材料和技藝,往往會將動物最顯著的特征呈現出來,從而突出其特征性和裝飾性,以此成為早期器物上最常見的裝飾元素之一。許多出土器物上精美的動物形象設計得頗具動勢和藝術性,完全可以代表當時的繪畫發展水平。第二卷對早期器物上的動物元素的含義進行了揭示,可以說這是本書最具創新性的部分,很多解釋極具啟發性。比如作者對饕餮紋含義進行了全新的詮釋,改變了以往將饕餮作為貪暴的象征。針對商代出現的大量鸮形青銅器,作者結合實物和相關文獻揭示出鸮類如何從辟邪猛禽一步步淪為傳統文化中不祥之鳥。第三部分深刻地反映出作者將出土器物與傳統文獻緊密結合的治學能力。比如,作者通過山西石樓出土龍觥上裝飾的龍蛇紋以及文獻記載,將其判定為夏文化遺存的明證。作者又根據“驅虎、豹、犀、象而遠之”的記載深入揭秘了商周之際民族遷徙的歷史事件。第四卷則是全書最具博物學特征的部分,作者通過岳石文化陶器上的葉脈印痕鑒定還原了古人生活的生態環境;商代貘尊的鑒定間接證實了貘在中國古代的分布;戰國銅鑒上的紋飾則反映了當時人們對居住環境的園林景觀營造;最有趣的是作者在云南江川李家山出土的蟲獸紋臂甲上發現了類似于今天“食物鏈”的動物圖案。這些有趣的發現不僅僅反映出作者對出土文物細致地觀察態度,更能展現出他廣博的知識和開闊的研究眼界,這些都是當下越來越專門化研究所需要的學術素養。
《文物中的鳥獸草木》中匯編的文章都是劉敦愿先生在20世紀中后期陸續完成的作品,從這些研究的內容可以看出有一些文章是其深入探討力求攻克的學術問題,有一些則是他對某一發現頗感興趣,隨機撰寫的短小雜文。對于前者他力求嚴謹完善地進行證實,有時還會引用國外相關案例進行間接證明;而對于后者文風就相對輕松,作者似乎在展示自己發現的同時又拋出一個問題,期待后來者可以對此產生興趣并將其解密。無論是作者撰寫的哪一類文章,無不流露出作者對這一議題的關注和熱情,學術研究的真諦本身就在于個人的志趣愛好與問題意識的緊密結合,只有很好地將兩者結合在一起,研究者才能自樂其中而源源不斷地收獲豐碩的果實,我想劉敦愿先生應該就是這樣一個學者。他幾十年來能夠一直堅持自己的興趣導向,在幾乎沒人涉獵的研究領域不斷辛勤耕耘。可能在當時的環境下他對古物中動植物元素的研究并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這對當時考古學關注的中華文明探源等宏大議題并無顯著影響,但進入新時代以來隨著全球化的發展,每個地區的學者面對的不僅僅有自己切身相關的文化議題,還要以全球化的眼光來思考整個人類的文化和發展。在這其中,人與自然之間關系的議題逐漸成為全球學者共同關注的研究方向,它不再是細枝末節的個人學術喜好,而成為我們當今學術研究的“顯學”。在這種背景之下,越來越多研究者開始通過環境史、博物學史、物質史等頗具時代特色的研究視角來重新看待這些傳統的研究材料,而劉敦愿先生早已在幾十年前就以自己的個人志趣在這方面辛勤耕耘。今天他的研究工作越來越受到眾多領域學人的關注,而這本小書的出現就是對這種情形最生動的反映。
今天的學者和民眾越來越關注到自然這個曾經被認為是人類社會發展的“背景板”,而實際是人類生存和發展的依托,學術研究層面逐漸將其置于主角地位。先有專門書寫自然的自然文學出現,接著各個文史學科陸續將其作為研究對象;而民眾也將其融入到自己的現代生活之中,自然生態成為了踐行美好生活的響亮口號。“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是兩千多年前孔子對我們的諄諄教誨,千百年來無數有識之士將其作為自己的志業,鍥而不舍地在歷史中傳承發展,今天我們在閱讀《文物中的鳥獸草木》的過程中,深刻地體會著劉敦愿先生對這一教誨的躬身踐行,而我們也將承接起他的這一愿景繼續前行。
(作者為四川大學文化科技協同創新研發中心副研究員)

賬號+密碼登錄
手機+密碼登錄
還沒有賬號?
立即注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