釵黛重像的文化基因與文學(xué)創(chuàng)意
釵黛重像的文化基因與文學(xué)創(chuàng)意
——品讀《紅樓十五釵》中的視角與新見
曹立波(中央民族大學(xué)文學(xué)院教授)
《紅樓夢(mèng)》通過(guò)人物塑造來(lái)體現(xiàn)華夏雅文化,應(yīng)為古今多數(shù)讀者的共識(shí)。但如何體現(xiàn)文化之雅,評(píng)論者往往見仁見智,亦如“一千個(gè)讀者就有一千個(gè)哈姆雷特”。哪些讀者眼中的“哈姆雷特”,或者寶黛釵,更接近作者的理想呢?這是一個(gè)值得探討的問題。正如歐麗娟教授在新作《紅樓十五釵》(下文簡(jiǎn)稱為“歐文”)前言中所云:“并不是每一個(gè)哈姆雷特都有價(jià)值,更不是憑感覺望文生義,就可以產(chǎn)生一個(gè)哈姆雷特。如果沒有全面掌握文本內(nèi)容,真正理解曹雪芹的意圖,那就只能永遠(yuǎn)在故事的真相之外。更遺憾的是,你會(huì)錯(cuò)過(guò)靠近雅文化的機(jī)會(huì)。”
歐文以紅樓人物為切入點(diǎn),考察賈寶玉及正、副冊(cè)諸女子,意在改變“流于世俗”的紅學(xué)解讀,重塑紅樓女性形象,感知貴族生活的雅與美。筆者作為同好,品讀《紅樓十五釵》中的視角與新見,有感而發(f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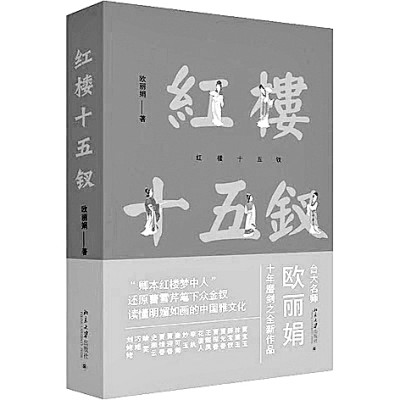
《紅樓十五釵》
歐麗娟 著
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
從人物重像到文化基因
曹雪芹植根于傳統(tǒng)文化,塑造了千姿百態(tài)的紅樓群芳。不同于我在《紅樓十二釵評(píng)傳》中以詩(shī)評(píng)人、以花喻人的評(píng)價(jià)方式,麗娟教授提出重像視角,即選取書中外貌性格相似者或古代文人雅士,與眾金釵進(jìn)行映射、類比,以重新理解紅樓佳人。
書中寶黛釵等諸多形象考論多涉及重像手法,如從家族、人生、婚戀三個(gè)方面,認(rèn)為賈寶玉的重像有榮國(guó)公、甄寶玉與薛寶釵。林黛玉的重像從形到神相對(duì)較多,既有“貌合”的晴雯、尤三姐,又有“情投”的妙玉、茗玉,也有西施、飛燕、娥皇女英等歷史人物,用這些紅顏薄命而才華出眾、性情高傲的女性,來(lái)烘托黛玉的才情貌。相較而言,歐文偏愛薛寶釵、賈探春這類德才兼?zhèn)涞呐樱渲叵穸嗳∽怨糯奈娜搜攀俊=钘铄♀O之美貌,以孔子之“時(shí)”、屈原之“潔”、陶淵明之“雅”,言寶釵之情性,贊美其周全大體、藏拙含蓄的“山中高士”之風(fēng)。贊賈探春為“泱泱大氣的將相雅士”,選顏真卿、王羲之、蘇東坡等名士來(lái)映襯其“才自精明志自高”的磊落人格。重像來(lái)源眾多,有的是借人物之口直接道出,如王夫人曾言晴雯眉宇間長(zhǎng)得像林黛玉;有的是作者在回目中點(diǎn)明,如第二十七回的“滴翠亭楊妃戲彩蝶,埋香塚飛燕泣殘紅”;重像解讀法將諸釵合成群像,豐富了個(gè)體形象的內(nèi)涵,較之前人的影子說(shuō),更富有系統(tǒng)性。
通過(guò)“重像”,讀者既可感受“本”與“像”多角度的相似性,同時(shí)也能品析作者對(duì)人物的褒貶態(tài)度。擁黛還是擁釵,自清代起,讀者爭(zhēng)議不斷。《三借廬筆談》記載鄒弢和老友許伯謙,就曾因此“一言不合,遂相齟齬,幾揮老拳”。擁黛者憐顰卿身世而愛其聰穎,貶釵襲之柔奸,如涂瀛稱“林黛玉人品才情,為《紅樓夢(mèng)》最”。擁釵者多愛釵襲穩(wěn)重而寬厚,憎晴黛之乖僻,如王希廉評(píng)“黛玉一味癡情,心地偏窄,德固不美,只有文墨之才;寶釵卻是有才有德”。近代俞平伯云:“書中釵黛每每并提,若兩峰對(duì)峙雙水分流,各盡其妙莫能相下。”他提出的“釵黛合一”說(shuō),影響至今。
在釵黛擁抑的問題上,給寶釵以應(yīng)有的褒揚(yáng),是值得肯定,也是達(dá)成共識(shí)的。就此,歐麗娟教授提出要打破“讀者的刻板印象”,“重新理解紅樓人物”,為釵襲翻案。
讀者若要客觀看待釵黛擁抑問題,還應(yīng)回歸文本尋找依據(jù)。脂硯齋曾言:“釵黛名雖兩個(gè),人卻一身,此幻筆也。”在作者心目中,釵黛二人本無(wú)高下之分,其中蘊(yùn)含著作者主張儒道兼美的審美理想。總之,紅樓佳人身上兼具豐富的文化基因,由此升華為具有永恒藝術(shù)魅力的文學(xué)意象或藝術(shù)符號(hào)。
從才子佳人到世道人心
《紅樓夢(mèng)》的情節(jié)雖以寶黛釵愛情故事為中心,但超越了傳統(tǒng)的才子佳人小說(shuō)。在佳人形象上,更凸顯女兒們的獨(dú)立審美價(jià)值;在主旨大意上,意在破陳腐舊套。歐文認(rèn)為《紅樓夢(mèng)》的主題宏大,有益于世道人心,解讀《紅樓夢(mèng)》時(shí)要“作高一層”,并“用學(xué)問一提”,認(rèn)定其深層次的內(nèi)涵應(yīng)為“展示雅文化之美,以及最終卻失落了而感傷哀挽”,并非簡(jiǎn)單地反對(duì)封建禮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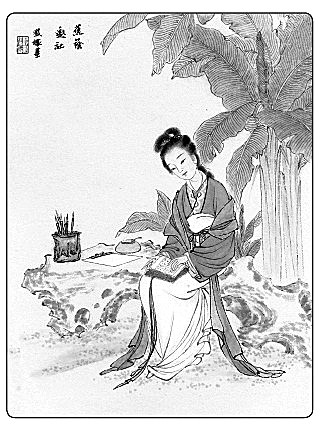
蕉蔭邀社 譚鳳嬛畫
歐文對(duì)寶黛釵愛情故事給予獨(dú)到解讀,認(rèn)為寶黛愛情是青梅竹馬友情的升華,而金玉良緣是和尚傳達(dá)的天作之合的神諭,寶釵不僅與寶玉有夫妻相,而且是他真正的同道,也是其出世思想的啟蒙者。曹雪芹在第五十八回特提“茜紗窗真情揆癡理”,讓寶玉明白個(gè)人的愛情可以安放于心中,與社會(huì)責(zé)任并不沖突。因此后文金玉良緣取代木石前盟乃有伏筆在先。后40回中“苦絳珠魂歸離恨天,病神瑛淚灑相思地”所設(shè)計(jì)的情節(jié)是違反小說(shuō)家原意的。
回歸文本可以得知,小說(shuō)中寶玉有玉,寶釵有金鎖,湘云有金麒麟……第五十七回寶釵得知探春給邢岫煙玉佩后,說(shuō)道:“他見人人皆有,獨(dú)你一個(gè)沒有,怕人笑話,故此送你一個(gè)。”眾姊妹都有的裝飾品,為何唯獨(dú)黛玉沒有?寶黛二人初見就發(fā)生了一場(chǎng)砸玉的風(fēng)波,書中屢屢提及黛玉對(duì)金玉之說(shuō)耿耿于懷,種種筆墨定非虛設(shè)。作者用金玉指代世俗標(biāo)準(zhǔn)下物質(zhì)聯(lián)姻的婚姻生活,而木石前盟則代表著心心相印的純真愛情,綜合全書考慮作者是否意在以無(wú)待寫有情?《莊子·逍遙游》篇中“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游無(wú)窮者”,好似寶黛木石前盟般超越物質(zhì)的知己愛情。通過(guò)對(duì)比營(yíng)造出“此時(shí)無(wú)聲勝有聲”的愛情理想,此乃作者突破中國(guó)古代才子佳人小說(shuō)婚戀情節(jié)的創(chuàng)新之處。
作者用史筆將真事隱去,構(gòu)建出的大觀世界,寄托著曲折幽深、內(nèi)涵廣闊的主旨大意,其中不僅包括人生價(jià)值的毀滅,愛情理想的破滅,眾女子青春與美的隕落,還包括貴族家庭沒落的悲劇。秦可卿是眾女子中情節(jié)設(shè)置少而全,也令人困惑的一個(gè)人物形象。她屬于兼容釵黛的“重像”,但歐文的解讀,似與文本存在距離。歐文批駁索隱派,認(rèn)為可卿乃皇家出身的說(shuō)法“已經(jīng)脫離了文本,完全缺乏小說(shuō)本身的證據(jù),何況清朝的歷史上也沒有類似的記載,等于是另外編造出來(lái)的故事,所以不宜相信”。這一觀點(diǎn)尊重文本與歷史,是客觀的。那么秦業(yè)為何收養(yǎng)可卿?歐文給出的解釋是,“秦可卿根本就是秦業(yè)自己的私生女……明白了這段隱情以后,便不要穿鑿附會(huì),也不要再用棄嬰來(lái)解釋秦可卿的性格和處境了”。從批駁索隱派出發(fā),歐文對(duì)“隱情”的主觀追索,似存在步入一種另類“穿鑿附會(huì)”的趨勢(shì)。筆者以為曹雪芹意在通過(guò)寫秦可卿作為養(yǎng)生堂抱來(lái)的女嬰,這種難知父母的身世背景,突出其雖兼有釵黛之美,但實(shí)則比香菱、晴雯等人物更加可憐,以此來(lái)寫秦氏與眾不同的命運(yùn)與個(gè)性,千個(gè)女子,千種不幸,以不幸寫個(gè)性,這是作者的藝術(shù)創(chuàng)意。深刻的藝術(shù)家總是試圖揭示人性,反思他們所處的世界、社會(huì)及其自身,因此真正優(yōu)秀的文學(xué)作品往往能夠反映世道人心,甚至上升到哲學(xué)層面,給人以啟迪。
從文本闡釋到傳播發(fā)展
《紅樓夢(mèng)》中形象鮮活的藝術(shù)生命、曲折細(xì)致的故事情節(jié),帶給讀者以美的享受。歐文在鑒賞時(shí)的語(yǔ)言風(fēng)格也獨(dú)具特色,其中既體現(xiàn)著作者新穎的欣賞角度,同時(shí)也折射出文本闡釋的多重魅力。
以冷香丸為例。歐文認(rèn)為冷香丸用來(lái)治療寶釵“從胎里帶來(lái)的一股熱毒”,它全部藥材用“十二”作為重量單位,象征著涵蓋所有金釵的悲劇命運(yùn),同時(shí)“冷”為“冷靜”,“香”是美好芳香的意思,用來(lái)暗示寶釵高潔的道德情操。這些理解頗有見地,但是也會(huì)引發(fā)思考。作者是否也意在通過(guò)藥丸揭示寶釵性格特征中某些冰冷淡漠的方面,從而側(cè)面展示其人物特質(zhì)?正如脂批所評(píng):“待人接物不親不疏,不遠(yuǎn)不近,可厭之人未見冷淡之態(tài),形諸聲色;可喜之人亦未見醴密之情,形諸聲色。”當(dāng)然,讀者并不能簡(jiǎn)單地用“非黑即白”的視角看待寶釵,寶姐姐身上富有樂于助人、溫柔敦厚、善解人意等美好品行,歐麗娟教授對(duì)寶釵形象的重新解讀是深細(xì)的。《紅樓夢(mèng)》塑造人物的高超之處在于人物形象是圓形的、真實(shí)的,而非片面的、虛假的,就如現(xiàn)實(shí)生活中每一個(gè)鮮活靈動(dòng)的個(gè)體,優(yōu)點(diǎn)與缺點(diǎn)并存,復(fù)雜與矛盾交織。

壽怡紅群芳開夜宴 譚鳳嬛畫
選自《紅樓十二釵評(píng)傳》
關(guān)于后40回,作者在《紅樓十五釵》中也表達(dá)了自己的見解。據(jù)筆者統(tǒng)計(jì),麗娟教授45萬(wàn)余字的著作,引用《紅樓夢(mèng)》原文內(nèi)容共300余處,涉及后40回評(píng)價(jià)的僅4處,占1.2%。雖然歐文也肯定后40回部分筆墨優(yōu)美,感人至深,但更樂于推薦閱讀前80回內(nèi)容。而關(guān)于人物結(jié)局等問題,歐教授多結(jié)合脂批加以推斷。重視脂批乃理所應(yīng)當(dāng),但這里存在兩個(gè)問題:一是從嚴(yán)格意義上講,后40回是否為高鶚?biāo)m(xù)還有待商榷;二是《紅樓夢(mèng)》經(jīng)典化進(jìn)程,離不開程本在傳播史上的貢獻(xiàn)。《紅樓夢(mèng)》120回本與前80回本相比,傳播領(lǐng)域較廣,影響范圍也較大。
縱觀有清一代百余年的《紅樓夢(mèng)》傳播史,由活字、木刻到石印、鉛印,印刷技術(shù)不斷更新,讀者對(duì)《紅樓夢(mèng)》的需求也不斷增多。由白文到增評(píng)、匯評(píng),版本內(nèi)容逐漸豐富,讀者對(duì)《紅樓夢(mèng)》的理解程度也在不斷加深。上述諸多印本,皆是以120回本的形式刊行的。因此僅就“截長(zhǎng)補(bǔ)短”和“補(bǔ)遺訂訛”寫出全書中心事件及主要人物悲劇結(jié)局,并“付之梨棗”而言,含有后40回的程本無(wú)疑是功大于過(guò)的。
基于不同版本的品紅文章異彩紛呈,盡管千人千解,對(duì)于紅樓文化之雅的認(rèn)知?jiǎng)t時(shí)有共鳴。在《紅樓夢(mèng)》版本的動(dòng)態(tài)軌跡上,每一階段猶如月亮的陰晴圓缺,各美其美。那么,文本研究是否亦應(yīng)客觀包容,美美與共呢?
(本文系2020年北京市民族藝術(shù)學(xué)高精尖學(xué)科項(xiàng)目【ART2020Y03】成果)
《光明日?qǐng)?bào)》( 2021年09月09日 11版)

賬號(hào)+密碼登錄
手機(jī)+密碼登錄
還沒有賬號(hào)?
立即注冊(c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