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詩人那么多,為什么只有杜甫集大成
談到我國舊詩演進發展的歷史,無疑唐代是一個足可稱為集大成的時代,只根據《全唐詩》一書來統計,所收的作者,就有二千二百余人之眾,而所收的作品,則更有四萬八千九百余首之多。在如此眾多的作家與作品中,其名家之輩出、風格之多采,自屬一種時勢所趨的必然之現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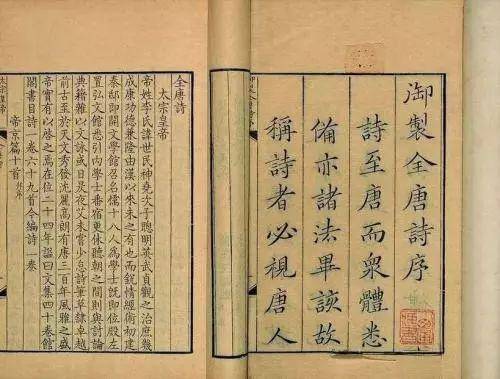
面對如此繽紛絢爛的集大成之唐代詩苑,如果站在主觀的觀點來欣賞,則摩詰之高妙,太白之俊逸,昌黎之奇崛,義山之窈眇,固然各有其足以令人傾倒賞愛之處,即使降而求之,如郊之寒,如島之瘦,如盧仝之怪誕,如李賀之詭奇,也都無害其為點綴于大成之詩苑中的一些奇花異草。
然而如果站在客觀的觀點來評量,想要從這種種繽紛與歧異的風格中,推選出一位足以稱為集大成的代表作者,則除杜甫而外,實無足以當之者。杜甫是這一座大成之詩苑中,根深干偉,枝葉紛披,聳拔蔭蔽的一株大樹,其所垂掛的繁花碩果,足可供人無窮之玩賞,無盡之采擷。

關于杜甫的集大成之成就,早自元微之的《杜甫墓志銘》、宋祁的《新唐書?杜甫傳贊》,以及秦淮海的《進論》,便都已對之備致推崇。此外就杜甫之一體、一格、一章、一句而加以贊美評論的詩話,歷代的種種記述,更是多到筆不勝書,至于加在杜甫身上的頭銜,則早已有了“詩圣”與“詩史”的尊稱,而近代的一些人,更為他加上了“社會派”與“寫實主義”的種種名號。
當然,每一種批評或稱述,都可能有其可資采擇的一得之見,只是,如果征引起來,一則陳陳相因,過于無味;再則繁而不備,反而徒亂人意。我現在只想簡單分析一下杜甫之所以能有如此集大成之成就的主要因素,我為其主要因素,實可簡單歸納為以下兩點:其一、是因為他之生于可以集大成之足以有為的時代,其二、是因為他之稟有可以集大成之足以有為的容量。
先從集大成的時代來說,一個詩人與其所生之時代,其關系之密切,正如同植物之與季節與土壤,譬如二月早放之夭桃,十月晚開之殘菊,縱然也可以勉強開出幾朵小花,而其瘦弱與零丁可想;又如種桑江邊,藝橘淮北,縱使是相同的品種根株,卻往往會只落得摧折浮海、枳實成空的下場,明白了這個關系,我們就更會深切地感到,以杜甫之天才,而生于足可以集大成的唐代,這是何等可值得欣幸的一件事了。
自縱的歷史性的演進來看,唐代上承魏晉南北朝之后,那正是我國文學史上一段萌發著反省與自覺的重要時期。在這一段時期中,純文學之批評既已逐漸興起,而對我國文字之特色的認識與技巧的運用,也已逐漸覺醒。上自魏文帝之《典論?論文》、陸機之《文賦》,降而至于鐘嶸之《詩品》、劉勰之《文心雕龍》,加之以周颙、沈約諸人對四聲之講求研析,這一連串的演進與覺醒,都預示著我國的詩歌,正在步向一個更完美更成熟的新時代。
而另一方面,自橫的地理性的綜合來看,唐代又正是一個糅合南北漢胡各民族之精神與風格而匯為一爐的大時代,南朝的藻麗柔靡、北朝的激昂伉爽,二者的相摩蕩,使唐代的詩歌,不僅是平順地繼承了傳統而已,而且更融入了一股足以為開創與改革之動力的新鮮的生命。這種糅合與激蕩,也預示著我國的詩歌將要步入一個更活潑更開闊的新境界。

就在這縱橫兩方面的繼承與影響下,唐代遂成為了我國詩史上的一個集大成的時代。在體式上,它一方面繼承了漢魏以來的古詩樂府,使之更得到擴展而有以革新;而另一方面,它又完成了南北朝以來一些新興的體式,使之益臻于精美而得以確立。在風格上,則更融合了剛柔清濁的南北漢胡諸民族的多方面的長處與特色,而呈現了一片多采多姿的新氣象。
于是乎,王、孟之五言,高、岑之七古,太白之樂府,龍標之絕句,遂爾紛呈競美,盛極一時了。然而可惜的是,這些位作者,亦如孟子之論夷、齊、伊尹與柳下惠,雖然都能各得圣之一體,卻不免各有所偏,而缺乏兼容并包的一份集大成的容量。
他們只是合起來可以表現一個集大成之時代,而卻不能單獨地以個人而集一個時代之大成,以王、孟之高雅而短于七言,以高、岑之健爽而不擅近體,龍標雖長于七絕,而他體則未能稱是,即是號稱詩仙的大詩人李太白,其歌行長篇雖有“想落天外,局自變生”之妙,而卻因為心中先存有一份“自從建安來,綺麗不足珍”的成見,貴古賤今,對于“鋪陳終始,排比聲韻”的作品,便爾非其所長了,所以雖然有著超塵絕世的仙才,然而終未能夠成為一位集大成的圣者。看到這些人的互有短長,于是我們就越發感到杜甫兼長并美之集大成的容量之難能可貴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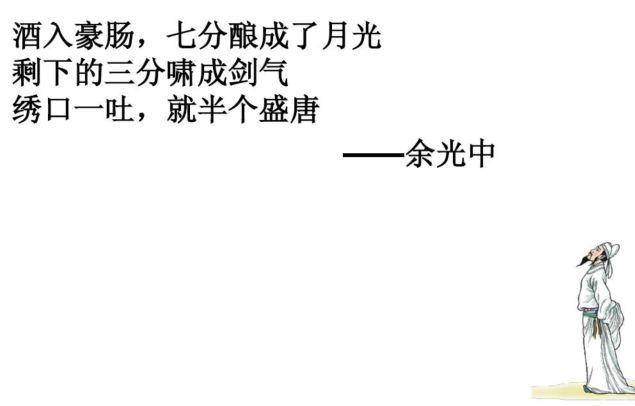
說到杜甫集大成的容量,其形式與內容之多方面的成就,固早已為眾所周知,而其所以能有如此集大成之容量的因素,我以為最重要的,乃在于他生而稟有著一種極為難得的健全的才性——那就是他的博大、均衡與正常。
杜甫是一位感性與知性兼長并美的詩人,他一方面具有極大且極強的感性,可以深入于他所接觸到的任何事物之中,而把握住他所欲攫取的事物之精華;而另一方面,他又有著極清明周至的理性,足以脫出于一切事物的蒙蔽與局限之外,做到博觀兼采而無所偏失。
這種優越的稟賦,表現于他的詩中,第一點最可注意的成就,便是其汲取之博與途徑之正。就詩歌之體式風格方面而言,無論古今長短各種詩歌的體式風格,他都能深入擷取盡得其長,而且不為一體所限,更能融會運用,開創變化,千匯萬狀,而無所不工。
我們看他《戲為六絕句》之論詩,以及與當時諸大詩人,如李白、高適、岑參、王維、孟浩然等,酬贈懷念的詩篇中的論詩的話,都可看到杜甫采擇與欣賞的方面之廣;而自其《飲中八仙歌》、《醉時歌》、《曲江三章》、《同谷七歌》、《桃竹杖引》等作中,則可見到他對各種詩體運用變化之神奇工妙;又如自其《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北征》及“三吏”、“三別”等五古之作中,則可看到杜甫自漢魏五言古詩變化而出的一種新面貌。

而自詩歌之內容方面而言,則杜甫更是無論妍媸鉅細,悲歡憂喜,宇宙的一切人情物態,他都能隨物賦形,淋漓盡致地收羅筆下而無所不包。如其寫青蓮居士之“飄然思不群”,與鄭虔博士之“樗散鬢成絲”,寫空谷佳人之“日暮倚修竹”,寫李鄧公驄馬之“顧影驕嘶”,寫東郊瘦馬之“骨骼硉兀”,寫丑拙則“袖露兩肘”,寫工麗則“燕子風斜”,寫玉華宮之荒寂,則以上聲馬韻予人以一片沉悲哀響;寫洗兵馬之歡忭,則以沉雄之氣運駢偶之句,寫出一片欣奮祝愿之情,其涵蘊之博與變化之多,都足以為其稟賦之博大均衡與正常的證明。
其次一點值得我們注意的,則是杜甫嚴肅中之幽默與擔荷中之欣賞。我嘗以為每一位詩人,對于其所面臨的悲哀與艱苦,都各有其不同之反應態度,如淵明之任化,太白之騰越,摩詰之禪解,子厚之抑斂,東坡之曠觀,六一之遣玩,都各因其才氣性情而有所不同,然大別之,不過為對悲苦之消融與逃避。其不然者,則如靈均之懷沙自沉,乃完全為悲苦所擊敗而毀命喪生。
然而杜甫卻獨能以其健全之才性,表現為面對悲苦的正視與擔荷。所以天寶的亂離,在當時一般詩人中,惟杜甫反映者為獨多,這正因杜甫獨具一份擔荷的力量,所以才能使大時代的血淚,都成為了他天才培育的澆灌,而使其有如此強大的擔荷之力量的,則端賴他所有的一份幽默與欣賞的余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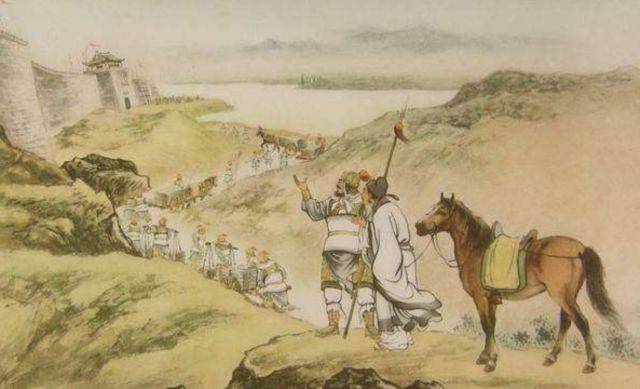
他一方面有極主觀的深入的感情,一方面又有極客觀的從容的觀賞,如其最著名的《北征》一詩,于飽寫沿途之人煙蕭瑟、所遇被傷、呻吟流血之余,卻忽然筆鋒一轉,竟而寫起青云之高興,幽事之可悅,山果之紅如丹砂,黑如點漆,而于歸家后,又復于囊空無帛、饑寒凜冽之中,大寫其幼女曉妝之一片嬌癡之。又如其《空囊》一詩,于“不爨井晨凍,無衣床夜寒”的艱苦中,竟然還能保有其“囊空恐羞澀,留得一錢看”的詼諧幽默。此外杜甫雖終生過著艱苦的生活,而其詩題中,則往往可見有“戲為”、“戲贈”、“戲簡”、“戲作”等字樣,凡此種種都說明了杜甫的才性之健全,所以才能有嚴肅中之幽默與擔荷中之欣賞,相反而相成的兩方面的表現。這種復雜的綜合,正足以為其稟賦之博大均衡與正常的又一證明。
此種優越之稟賦,不僅使杜甫在詩歌的體式、內容與風格方面達到了集大成之多方面的融貫匯合之境界,另外在他的修養與人格方面,也凝成了一種集大成之境界,那就是詩人之感情與世人之道德的合一。在我國傳統之文學批評中,往往將文藝之價值依附于道德價值之上,而純詩人的境界反而往往為人所輕視鄙薄。即以唐代之詩人論,如李賀之銳感,而被人目為鬼才,以義山之深情,而被人指為艷體,以為這種作品“無一言經國,無纖意獎善”(李涪《釋怪》)。
而另外一方面,那些以“經國”、“獎善”相標榜的作品,則又往往虛浮空泛,只流為口頭之說教,而卻缺乏一份詩人的銳感深情。即以唐代最著名的兩位作者韓昌黎與白樂天而言,昌黎載道之文與樂天諷諭之詩,他們的作品中所有的道德,也往往僅只是出于一種理性的是非善惡之辨而已。
而杜甫詩中所流露的道德感則不然,那不是出于理性的是非善惡之辨,而是出于感情的自然深厚之情。是非善惡之辨乃由于向外之尋求,故其所得者淺:深厚自然之情則由于天性之含蘊,故其所有者深。所以昌黎載道之文與樂天諷諭之詩,在千載而下之今日讀之,于時移世變之余,就不免會使人感到其中有一些極淺薄無謂的話,而杜甫詩中所表現的忠愛仁厚之情,則仍然是滿紙血淚、千古常新,其震撼人心的力量,并未因時間相去之久遠而稍為減退,那就因杜甫詩中所表現的忠愛仁厚之情,自讀者看來,固然有合于世人之道德,而在作者杜甫而言,則并非如韓、白之為道德而道德,而是出于詩人之感情的自然之流露。

只是杜甫的一份詩人之情,并不像其他一些詩人的狹隘與病態,而乃是極為均衡正常,極為深厚博大的一種人性之至情。這種詩人之感情與世人之道德相合一的境界,在詩人中最為難得,而杜甫此種感情上的健全醇厚之集大成的表現,與他在詩歌上的博采開新的集大成的成就,以及他的嚴肅與幽默的兩方面的相反相成的擔荷力量,正同出于一個因素,那就是他所稟賦的一種博大均衡而正常的健全的才性。

賬號+密碼登錄
手機+密碼登錄
還沒有賬號?
立即注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