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簡史》:名人故里文化精神之現代書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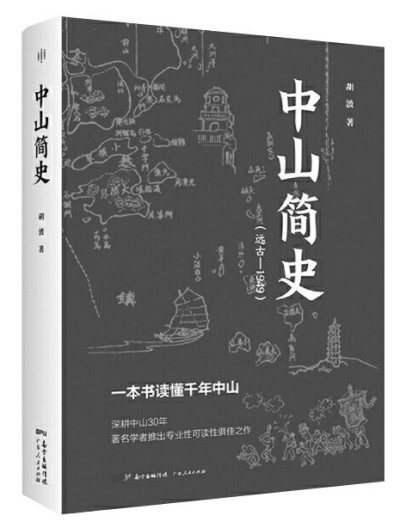
《中山簡史》,胡波著,廣東人民出版社2021年6月第一版,188.00元
文化是一座城市的靈魂。而名人故里具有豐富的文化資源。如何將名人故里的過去、現在和未來呈現出來,使得“古”時的歷史文化遺存與“今”時讀者的知識體系相貫通,在塑造名人文化形象、深入推進名人研究的同時,帶動城市整體文化研究和普及,達到“文化興城”的目的,是值得文化研究者深入探索的問題。歷史文化學者胡波的《中山簡史》就在此方面作出了非常有價值的探索。
2022年,是香山建縣870周年。香山,是廣東中山的古稱,南宋年間建縣,屬廣州府,轄今天的中山、珠海、澳門三地。進入近代,這片土地上誕生了一代偉人孫中山。
翻看介紹中山的現代史志,一般是這樣敘述的:“中山,古稱香山。南宋紹興二十二年(1152),朝廷正式設立香山縣。1925年,孫中山逝世,為紀念孫中山先生,香山縣更名為中山縣。1983年,中山縣改為中山市,1988年中山市升格為地級市,直屬廣東省管轄。”對許多中山人來說,香山設縣之前的歷史是混沌模糊的。考古研究已經表明,香山最早有人類活動的時間,可以追溯到四五千年前。南宋紹興二十二年上溯至四五千年前的這三千多年間,如何孕育出香山之海島淺灘和沙田陸地? 又如何孕育出香山海島之族群和品性? 又如何讓世代蟄居于此的香山人生生不息,靠海而生,又勇敢地遠渡重洋,在近代中國歷史中寫下濃濃重彩的一筆? 那絕不是《太平寰宇記》的一句“隔海三百里,地多神仙花卉,故曰香山”所能一筆帶過的。自2006年,胡波教授提出“香山文化”概念以來,香山之人與自然、人與文化之關系得到了越來越多的關注和研究,但是關于“香山為何”“何以香山”“何以中山”的話題仍然有很大的研究空間。
何以中山? 首先是有中山之地理,乃有中山之人。翻開《中山簡史》,首先吸引眼球的,就是作者對中山地理的精彩敘寫。“講述中山古代的歷史,追溯中山文化的源頭,不能不從它的地理環境開始。”作者以宏闊的文化視野,旁征博引,從人類文明演進的眼光來審視我們都習以為常的中山地形地貌、氣候水土,目的是梳理出自然物候與人文氣候之間的內在互動聯系。歷史空間中的人,當然是推進歷史演進的主要力量,但是先于人而存在的地理物候,卻是人類歷史畫卷不可缺少的底色。“歷史學首先是地理環境的史學。”從地理出發,這是中山歷代先輩修志之經驗。中山修志始于明朝永樂中期,到民國的500年間,共有近10次修志盛舉。明永樂中期由容悌與首創,后由黃經修訂的《香山縣志》,就是“詳于鳥獸草木”。清道光年間,黃培芳編纂《香山縣志》,更是將輿地提高到最為突出的地位。他說:“古之地志,專以地為主聿,重圖經。”所以,道光《香山縣志》“不離乎地志之宗,故繪圖必親歷開方,山川必審晰支脈,都鄉必細書里數,海防尤海疆所重,必特立專門”,為后代留下了非常珍貴的香山輿地圖說,讓我們還能清晰地了解兩百年前的山川地貌、河澤縱橫、風物名勝。《中山簡史》詳于地理,與歷代學人的香山史志書寫一脈相承。雖則如此,《中山簡史》的地理書寫,仍然是非常困難的事情,首先就難在史料之闕。“宋元以前的香山史料幾乎是大海撈針,考古發掘的文物、遺址和遺跡簡直屈指可數。”所以作者從地貌、遺跡、史料留存中,進行挖掘和闡釋。作者寫道:持續的地理變動,使得香山既生成了海島生態環境下的海洋文化,又孕育了陸地生態條件下的農耕文化;世居海岸的居民,形成了特定的情懷:“尊重家庭,維護傳統與熱愛新鮮事物相互交織,亦渴望像牧人那樣激蕩”……在流暢簡潔又充滿詩意和張力的語言敘述中,拓展了今人對古香山的想象空間,又嘗試回答了“何以中山”之問。
何以中山? 有中山之人,乃有中山之文化。“世界上只要有了人,就有了人間奇跡,就有了人類社會的歷史。”明朝初年,香山仍是偏僻海島,是渺無人煙之地。香山大學者黃瑜著《雙槐文集》,時任廣東按察司的趙宏認為,該書“將使香山之名與昌黎眉山并稱于世”。言下之意,香山之名不為人知,還得仰賴黃瑜之文名使之光大。明嘉靖年間,黃佐說:“敝邑褊小,僻在海隅。”由于遠離中原文化中心,香山的文化建設和傳播受到極大阻礙,所以,他纂修的《香山縣志》著重增修“名宦人物”,以彰香山之名教。可見,一地之文化,仰賴于一域之名人。在《中山簡史》中,人是根植于這片海島沙田的人,是面向海洋靠海而居的有著海洋文化性格的人。與其他史書不同,《中山簡史》并未刻意專章寫人物,而是將人物放到廣闊的歷史時空中去書寫。如,最早的香山鄉賢是東漢順帝時的陳臨,他守孝悌,舉孝廉,讀圣賢書,仁愛親民,官至廷尉(相當于全國最高法官)。陳臨的出現,正是中原漢人南遷、香山島開始從蠻荒之島到文治教化之邦轉換的結果。唐代進士鄭愚的時代,香山島已經是“舟船往返、人客紛至”的海島福地。正芳和尚開山古香林,正是佛教在嶺南地區得到廣泛傳播、中外文化交流日益頻繁的時期。陳天覺之于香山選址造城、清末留美幼童之于移民潮、革命偉人孫中山之于香山易名等等,在作者費心取舍編排的流暢敘事中,為我們呈現出一幅中山歷史發展演變的進程圖。何以中山? 正是生于斯長于斯的人們,面對世界變遷所作出的無數次選擇,面對人生順逆時所展現出的勇氣和心力,才使得中山成為中山。
《中山簡史》可以說是當代中山歷史書寫的創新之作。史和志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志書是求全,以史料保存為目的,而史書是學術性著述,注重于“述史”,追求勾勒歷史發展的脈絡,揭示歷史發展規律,要講清楚“為什么”。伏爾泰認為,歷史研究應實現一種哲學的或理論的理解。梁啟超開啟的新史學,主張打通學科界限,從社會、經濟、文化、宗教、地理、考古、心理等更廣闊的視野探求歷史。在《中山簡史》中,我們既看到作者作為史學家“述史”的扎實功底,又看到作為已出版30多部香山文化論著的文化學者跨學科研究的宏闊視野。英國史學家卡萊爾(Carlyle)把史學家劃分為兩種,一種是歷史學家中的藝術家,他們“以整體的觀念使一個領域變得崇高起來,為人們所熟悉并且習慣性地認識到,唯有整體中部分才能得到真正的確認”;一種是歷史學家中的匠人,他們看不到整體,也不覺得有整體。在《中山簡史》流暢的敘述中,始終貫穿著一個整體觀:“中山首先是珠江三角洲上的中山,也是嶺南天地下的中山,還是中國文化背景下的中山,更是全球化進程中的中山。”總之,閱讀《中山簡史》是愉悅的享受,一方面得益于其暢達的語言藝術,另一方面,得益于作者一以貫之的整體觀。

賬號+密碼登錄
手機+密碼登錄
還沒有賬號?
立即注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