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xué)刊物新年第一彈:“未來”已至,但文學(xué)的世界很現(xiàn)實(shí)
2020年乃至2020年代在許多科幻作品中都是“未來”的代名詞。如今現(xiàn)實(shí)已經(jīng)照進(jìn)2020,《人民文學(xué)》《收獲》《花城》《鐘山》《十月》《當(dāng)代》等主流文學(xué)刊物也以嶄新的面貌推出開年“第一本”。
它們有的重點(diǎn)推出“短篇小說專輯”,意在提醒讀者和評(píng)論家們重視當(dāng)前的短篇小說創(chuàng)作;有的關(guān)注“城市文學(xué)”,關(guān)注新城市、新人、新經(jīng)驗(yàn)為文學(xué)帶來的新變 革;有的作品呈現(xiàn)津味小說的十足煙火氣,有的刻畫中國底層百姓如何守護(hù)善的本能;有的采用現(xiàn)實(shí)主義寫法,有的試圖打破現(xiàn)實(shí)框架的實(shí)驗(yàn)……讓我們來看看這些 刊物與作家們關(guān)照的一切,在新年的第一個(gè)故事中如何呈現(xiàn)。

《人民文學(xué)》
津味小說,是當(dāng)代中國文學(xué)流脈的重要組成部分。尤其是二十世紀(jì)八十年代之后,馮驥才、林希等作家創(chuàng)作出一批引領(lǐng)文壇市井寫作風(fēng)潮的名作。這些作品以天津歷 史尤其是近現(xiàn)代市井、掌故為基本故事要素,具有天津性格特色的人物和切合天津時(shí)代變遷的豐富情節(jié)充盈其間,適量取用靈巧鮮活又容易意會(huì)的天津方言,津腔津 韻,蔚成大觀。
《人民文學(xué)》2020年第一期推薦的長篇小說《煙火》,就是這樣一部津味小說。作家王松將小說的時(shí)間背景放到了清末到抗戰(zhàn)勝利期間,人物大都是以手藝謀生 的胡同百姓,做拔火罐兒的老癟、刨雞毛撣子的王麻稈兒、狗不理包子鋪的高掌柜、绱鞋的老朱、打簾子的馬六兒、拉膠皮的保三兒、玩石鎖的劉大頭……當(dāng)然也有 靠歪門邪道謀利害人混跡市井的楊燈罩兒以及洋人、買辦各色人等,更有為民族大義不畏犧牲的英雄。歷史在一個(gè)普通又別樣的胡同內(nèi)外演進(jìn),人生命運(yùn)的希望、新 的世界的音信在“逝去的親人——回來的子女”的大架構(gòu)下,煙火十足地傳導(dǎo)給每一個(gè)閱讀的有心人。
“王松琢磨透了天津的風(fēng)俗文化和天津的人性物理,一切用滿是津味的細(xì)節(jié)說話,”《人民文學(xué)》的編者認(rèn)為,如果要找一部用“有用的細(xì)節(jié)”來講述故事、散發(fā)風(fēng)味、支撐結(jié)構(gòu)、立起人物的長篇小說的話,《煙火》就是一個(gè)好例。

《收獲》
“2019年盛夏,編劇安東陷入經(jīng)濟(jì)困境與精神迷茫之際,忽有一位操家鄉(xiāng)口音的男子以巨資投資安東下一個(gè)劇本。與此同時(shí),女科學(xué)家陸絲絲正在不惜一切代價(jià) 開發(fā)自己的兩個(gè)人工智能機(jī)器人,涓生和子君。安東家鄉(xiāng)的地下,埋藏著大量遠(yuǎn)古的鳥骨,他少年時(shí)期的友人M在地上建造著別出心裁的KTV。安東馬上要與之相 遇,不過在此之前,他恐怕要走很遠(yuǎn)的路。”
雙雪濤在2020年第一期的《收獲》中貢獻(xiàn)了這樣一個(gè)特別的故事——《不間斷的人》。很難定義雙雪濤的創(chuàng)作風(fēng)格,平實(shí)的、天馬行空的、魔幻的……讀者也總 是需要多走那么一步:永遠(yuǎn)不要盲目相信自己一時(shí)一刻的感覺和信奉一個(gè)故事本就該是情節(jié)和邏輯明晰的,充滿意趣的人物、有悖常理的情節(jié),雙雪濤似乎一直在做 著打破現(xiàn)實(shí)框架的實(shí)驗(yàn)。文本上,建立——打破——再建立,去盡情感受下雙雪濤為無限趨近于小說文本的極限所做的嘗試吧。
去年,青年作家中冒頭的班宇絕對(duì)算一個(gè)。在繼《逍遙游》之后,班宇在《收獲》發(fā)表了第二篇小說《夜鶯湖》。“寫作《夜鶯湖》時(shí),沒有明確緣由,小說像是從 天而降,或者脫水而出,一個(gè)溫暖的陰影,緩緩波蕩,從身后將我抱住。”班宇想,“文學(xué),或者寫作,在這里到底扮演著什么樣的角色?也許不過只是一束稻草的 影子,沒法攀附,更談不上拯救了,只是在漫長、趨于空白的等待時(shí)間里,與自己做的一點(diǎn)游戲。”

《花城》
隨著城市化進(jìn)程的推進(jìn),越來越多的作者開始書寫城市,他們?cè)诔鞘形膶W(xué)中追尋自我與認(rèn)同,探索城市與人的關(guān)系。城市文學(xué)是相對(duì)年輕的,遭遇著缺乏精神層面敘事、刻板化書寫城市生活的機(jī)械性、商業(yè)與欲望對(duì)人的異化等等批評(píng)。
青年作者應(yīng)該如何回應(yīng)當(dāng)下的城市?在近現(xiàn)代城市的被觀看和展示的譜系上,什么是當(dāng)今青年一代的“我城”?又如何書寫每個(gè)人不同的,屬于自己性別、代際、階 層的“我城”?《花城》2020年第一期可謂“八城記”,由評(píng)論家何平主持的“花城關(guān)注”著眼于“ ‘我城’的兒女們”,邀請(qǐng)到笛安、班宇、王占黑、郭爽、林秀赫、陳苑珊、楊則緯、朱婧等一批青年作家來書寫城市。
朱婧的《先生 先生》,書名命題也是為小說命意,做著舊學(xué)問的寧先生,也許只有在南京這樣的古都才毫無違和,而在北京和南京旅行的雙城記,“先生”和“古都”只能是一闋 挽歌,唯有舊日子值得珍惜,而舊日子正在流逝;笛安在《我認(rèn)識(shí)過一個(gè)比我善良的人》塑造的人物,即是新“北京人”,也是來自在“小地方“的無根漂泊者;班 宇的《羽翅》可以理解成一次氣息微弱的呼救,反抗被規(guī)訓(xùn)和掩埋,因?yàn)樯蜿栔诎嘤睿膫€(gè)人記憶可能是鐵西區(qū),也可能是少年時(shí)代幾個(gè)人隱秘的音樂社區(qū);王 占黑的《去大潤發(fā)》,城市的地方性已經(jīng)被侵蝕得很淡,就像林秀赫的《蕉葉覆鹿》中,舉凡網(wǎng)紅作家、粉絲、暢銷書、手游、直播、LINE……發(fā)生在中國的一 個(gè)小城,也是整個(gè)中國的青年亞文化的現(xiàn)場(chǎng)。城與城趨近,但更隱秘的差異性也被年輕的作家打撈出來。

《鐘山》
《鐘山》2020年第一期重點(diǎn)推出“短篇小說專輯”,集中刊發(fā)韓東、劉慶邦、畢亮、陳思安等多位小說家的短篇佳作,希望以此提醒讀者和評(píng)論家們重視當(dāng)前的 短篇小說創(chuàng)作。在《鐘山》看來,相較于長篇小說長期受到各種評(píng)論、評(píng)獎(jiǎng)、排行榜等經(jīng)典化機(jī)制的“追捧”,短篇小說的關(guān)注度一直不高,這與短篇小說在當(dāng)下所 取得的藝術(shù)成就是不匹配的。
此外,2020年《鐘山》恢復(fù)了它曾經(jīng)卓有影響的“河漢觀星”欄目,再度以真誠的觀點(diǎn)和鮮明的立場(chǎng),倡導(dǎo)文學(xué)批評(píng)的“在場(chǎng)”和“理性”。第一期推出的是張學(xué)昕的《阿來論》。從2020年起,《鐘山》還新增兩個(gè)專欄:潘向黎的“如花在野”和范培松的“文學(xué)小史記”。
去年年底,第二屆中國江蘇·揚(yáng)子江作家周在南京開幕。在《鐘山》新年第一期“特稿”中,張大春、多米尼克·西戈(法)、阿來、畢飛宇、西蒙·范·布伊(英)、李修文等作家在作家周“文學(xué):穩(wěn)定與變化”主題論壇上的主旨發(fā)言將被全文披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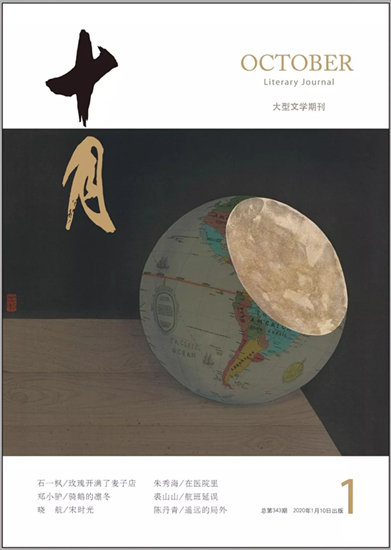
《十月》
《十月》2020年第一期主推的是石一楓的作品《玫瑰開滿了麥子店》。在這個(gè)故事里,沿著鐵路線漂流到都市的鄉(xiāng)下女孩王亞麗,在親情與愛情的雙重剝削下, 主動(dòng)選擇“團(tuán)契”的蹭飯生活。這是石一楓《心靈外史》之外的強(qiáng)大而堅(jiān)韌的“不信史”:不同于“大姨媽”的另一種中國底層百姓,在人生最艱難的時(shí)刻拒絕成為 乞討者,拒絕報(bào)團(tuán)取暖的誘惑,在強(qiáng)者面前保持清明的自我。從最低處升起的,不是“信”的玫瑰,是被侮辱與被損害之后依然頑強(qiáng)生長的善的本能。
此外,《十月》刊載了鄭小驢的《騎鵝的凜冬》、曉航的《宋時(shí)光》、朱秀海的《在醫(yī)院里》、裘山山的《航班延誤》這幾部中短篇小說。陳丹青紀(jì)念木心恢復(fù)寫作 35周年的《遙遠(yuǎn)的局外》與陳洪金的《金沙江的幽暗處》則是散文精品。在“思想者說”欄目中,黃燈帶來關(guān)注地方普通高校學(xué)子生存現(xiàn)狀的新作《班主任》:教 育改變階層的上升渠道被封鎖之后,底層學(xué)子踩在個(gè)人奮斗的鋼絲繩上,困守日益緘默的青春。
還值得關(guān)注的是,2020年《十月》“譯界”欄目將呈現(xiàn)詩歌之外更多類型的外國文學(xué)新作。第一期刊介的是美國作家羅伯特·斯通的短篇小說《幫助》,譯者李寂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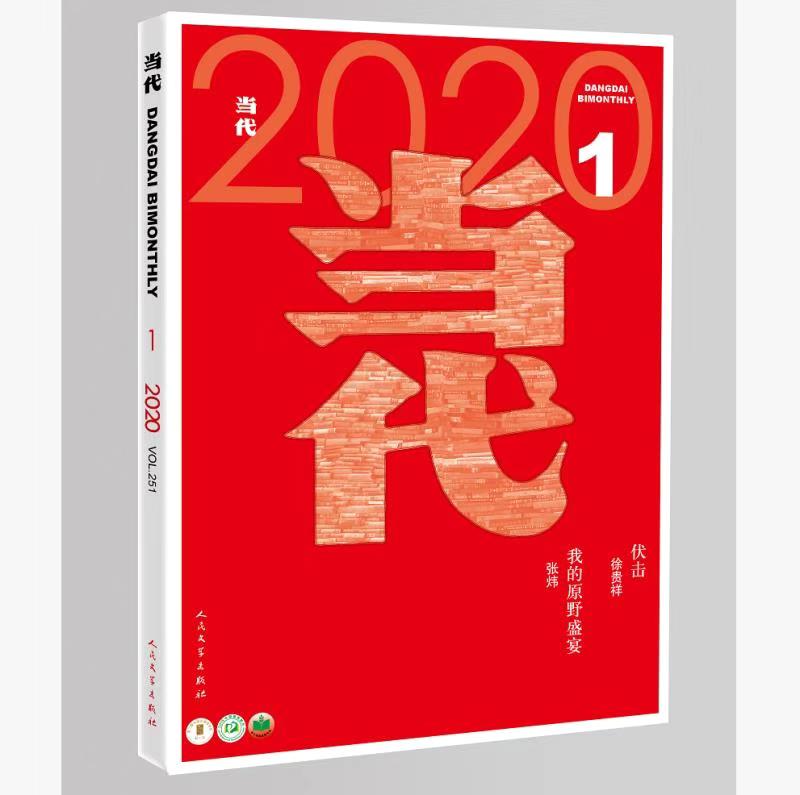
《當(dāng)代》
《當(dāng)代》2020年第一期主推的是徐貴祥的作品《伏擊》。小說描寫了國民黨特務(wù)易水寒冒充犧牲的紅軍戰(zhàn)術(shù)專家,在陜北潛伏的日子里感受到紅軍崇高的信仰、抗戰(zhàn)的真誠后,調(diào)轉(zhuǎn)槍口,在對(duì)日抗戰(zhàn)中多次以死洗罪、向死而生,最終加入共產(chǎn)黨,為民族存亡浴血奮戰(zhàn)。
作為徐貴祥戰(zhàn)爭(zhēng)系列的一部,《伏擊》采用現(xiàn)實(shí)主義寫法,關(guān)注大時(shí)代,和《當(dāng)代》一以貫之的氣質(zhì)非常吻合,或許更得男性讀者偏愛。曾創(chuàng)作《歷史的天空》等名篇的軍旅作家徐貴祥近兩年也重新進(jìn)入了比較高產(chǎn)的創(chuàng)作階段,無論創(chuàng)作數(shù)量還是質(zhì)量都值得關(guān)注。
此外,本期《當(dāng)代》還刊發(fā)了張煒的長篇紀(jì)實(shí)文學(xué)《我的原野盛宴》、孫睿的中篇小說《酥油和麻辣燙》等作品。《我的原野盛宴》以深情、詩意、輕盈的筆調(diào)回憶 自己的少年時(shí)光,描畫出一個(gè)充滿生命精靈的美麗世界。《酥油和麻辣燙》寫一個(gè)步入中年的女人,已經(jīng)成為公司中層領(lǐng)導(dǎo),正當(dāng)事業(yè)上升期時(shí),卻突然發(fā)現(xiàn)自己得 了胃癌,并且立即決定辭去工作去西藏做一次長途旅行。在旅行過程中,結(jié)識(shí)了當(dāng)?shù)匦』镒拥ぴ觯c他展開了一段感情,回京后發(fā)現(xiàn)自己懷孕了。此時(shí)的“我”對(duì)生 命又有了另一種認(rèn)識(shí)。

賬號(hào)+密碼登錄
手機(jī)+密碼登錄
還沒有賬號(hào)?
立即注冊(c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