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永新著《一個人的文學史》11年后再版 見證一群人在文學史里前行、成長和變化
見證一群人在文學史里前行、成長和變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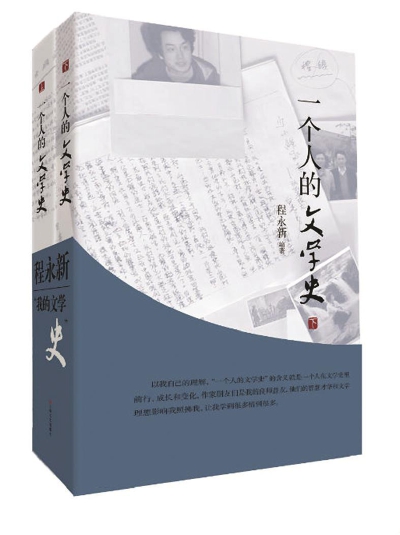
1988年,作家余華給時任《收獲》雜志編輯程永新寫信表示,他很欣賞1987年的《收獲》第5期,亦即后來被命名為“先鋒文學專號”的這一期。余華說:“我一直希望有這樣一本小說集,一本極端主義的小說集。中國現在所有有質量的小說集似乎都照顧到各個方面,連題材也照顧。我覺得你編的這部將會不一樣,你這部不會去考慮所謂客觀全面地展示當代小說的創作,而應該是顯示出一種力量,異端的力量。”
在次年的信件中,余華再次表示,他非常認可程永新推陳出新的舉動,“你想換一批人的設想挺棒。現在確有一批更新的作家”。與此同時,他也表現出對被稱為“先鋒小說”的作品的擔憂:“我擔心剛剛出現的先鋒小說會在一批庸俗的批評家和一些不成熟的先鋒作家努力下,走向一個莫名其妙的方向。新生代作家們似乎在語言上越來越關心,但更多的卻是沉浸在把漢語推向極致以后去獲取某種快感。……現在用空洞無物去形容某些先鋒小說不是沒有道理。”
這兩封信收錄于近期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的《一個人的文學史》。同名著作曾于2007年出版,腰封上赫然寫著“中國第一部‘個人文學史’、‘80后’的文學補課教材”的宣傳語。在日前于上海光的空間書店舉行的再版新書發布會上,該書作者、《收獲》雜志主編程永新表示:“當時出版圈流行‘一個人的××’,我起初是不同意這個名稱的,覺得太浮夸了,但出版商說這樣書會賣得好。我就同意了。”一晃11年過去了,這次推出的修訂版換了三分之一的內容,也增加了篇幅,收錄程永新以“與文學有關”為原則篩選出來的,數十年間與諸多作家來往的書信,下本主要收錄他參加各種文學活動寫的評論文字。為增強現場感和生動性,他還把網絡上與作家的交流內容收了進來,例如微博、微信。與此同時,這次修訂縮小了雜志部分。書名沿襲了舊例,腰封文字則變成了“一個人的文學史的含義,就是一個人在文學史里前行、成長和變化”。
在某種意義上,這本書收錄的書信,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余華、蘇童、王朔、馬原等作家在文學史里的“前行、成長和變化”。馬原表示:“80年代是屬于我們的80年代,當年我們意氣風發,都是小伙子,現在我明顯是一個老人了。我們這一代人整個歷史過去了,程永新作為見證人,把寶貴的東西留了下來。”
確如其言,彼時他們初露才華、青春年少,其鮮明的個性與風格都在往來信件中有所體現。余華在他的信里透露出他對當時中國先鋒小說創作的反思與批評,更多作家的信件則談的是他們在寫作上的探索。比如,1986年11月,鐵凝在給程永新的信中坦言:“編輯部和一些文學同行能夠喜歡《麥秸垛》,令我感到欣慰。能夠超越自己而又不失卻自己是極艱難的,我努力在做,也不知下一步會如何。有朋友們的鼓勵,走起來便踏實了許多,這是真話。”
有時,作家們也會透露自己即將開始的寫作歷程。蘇童在1986年的信中就提到自己正要“開始搞”家族史《一九三四年的逃亡》,“要把我的諸多可愛不可愛的親人寫進去,但也許因為太認真太緊張,竟然不能像寫短篇那樣順,寫起來真是痛苦要發神經的樣子,但也許真情流露只此一回,所以我揣著現有的兩萬字像揣著一個妖魔”。他還不無風趣地告訴程永新,他的第一篇小說《青石與河流》在《收獲》刊發后,“好多人似乎是一下子認識了我,使我面部表情一陣抽搐”。
而王朔則與程永新就修改意見進行了富有生趣的“討價還價”。他的小說《頑主》原名《五花肉》,當時已經送審,但程永新覺得題目不好,就與王朔商量,后來王朔擬了三個題目,程永新挑中了《頑主》。在1987年的一封書信中,王朔回復他的提議道:“這篇小說我想會使正人君子有不好的感覺,所以名字盡可能鄙一些……”信件末尾還不忘以上海話“謝儂謝儂”致謝。在1991年的一封信件中,他又對程永新的修改“咬牙切齒”道:“你知道就連醫生也很難給自己孩子下手開頭,在我已屬咬牙黑心了,但可能仍有余贅……老兄閱稿時務請費心剪草除根,最后清掃一遍。”
由此,這些充滿溫度的書信就像馬原說的,讓文學史本身有了溫度。“我也當過中文系老師,老師們講文學史,上說秦皇漢武,下說莫言鐵凝,一點溫度都沒有。但是讀這本書的時候,恰好里邊有一點關于馬原的短篇,你會讀到作為一個小伙子的馬原、一個二十幾歲的馬原。”他還說:“我不知道程永新做這部書的時候有沒有想起過陳村的一句評價:《收獲》是中國當代文學的簡寫本。真是非常奇妙,程永新見證了從1982年以來圍繞這本雜志所有的沸騰的文學時間。”
但一開始,對于把這些有溫度的書信整理出來,程永新是有些顧慮的。本世紀初,在北京三里屯的酒吧里,出版人丁小禾對他說:“你在文壇幾十年,應當將那么多具有現場感的東西整理出來。”這個提議讓程永新有些不置可否。他不知道公開作家書信是否有版權問題,也不清楚給作家寫過的那無數探討作品的信件還能不能找到。回到上海之后,他給余華打了電話,問他那兒是不是還保存著自己的信,結果被澆了一頭冷水:“誰像你幾十年都待在一個辦公室里,我已經搬了三次家,很難保存信件的。”
程永新確實在一個辦公室里待了幾十年。他從1982年起就到《收獲》雜志社實習,將所有與作家的通信都放置在了一個柜子里。在丁小禾的催逼下,程永新開始閱讀整理這些信件。“這一看讓我感觸很深,仿佛看到自己從年輕時代慢慢成長,每個作家朋友的樣子也恍若在眼前。”他對將作家私人信件公之于世這件事反復掂量,“假如對未來的寫作者或者研究者能夠提供一些具有現場感的細枝末節,是不是還真有一些史料價值?”
毋庸置疑,誠如文學評論家王堯所說,這部書敞開了文學史的研究空間,某種意義上,原生態地呈現了文學生產的過程。“多少年來,在我們的批評里,在文學史著作里,這部分是缺失的。文學史是獨斷專行的文學史,人們沒有仔細討論過這些文本是如何產生的。”從這個意義上,王堯認為,讀懂了《一個人的文學史》,才能讀懂近40年的中國文學。“這部書我以為不可替代。”
對一些不曾親歷80年代的寫作者來說,這本書同樣有著不可替代的價值。剛獲得第七屆魯迅文學獎散文獎的作家李修文表示,他1998年認識程永新,至今有二十年了。“在他身邊,我還認識了一批作家,比如阿城。對于一個當時還沒有認真打算一輩子寫作的年輕人來說太燦爛了。”更重要的是,如李修文所說,“70后”作家基本上都是看著《收獲》開始寫作的,這至少決定了他自己身上的兩種特質。一是,不管寫得怎樣,他都不會降低對于什么是真正的文學的尺度。二是,在漫長的個人生活和創作歲月里,就算他沒有寫,《收獲》也是他近在眼前的一個尺度。“這個尺度時時刻刻在拷問著我的寫作,也在拷問我們這一代作家的寫作。”
雖然如此,程永新謙稱,職業文學編輯就是作家忠實的讀者和提衣人,作品的成功只屬于作家。“作家朋友們是我的良師益友,他們的智慧才華和文學理想影響我照拂我,讓我學到很多悟到很多。”回顧曾經80年代的火熱文學激情,程永新直言:那種獨特的熱畢竟是無法重現了,“文學的小道上已經非常擁擠。今天我們可干的事情太多了;當年是沒事可干,很多人通過寫作來改變命運。但我們期待那份對文學藝術的執著和精進,會一直延續下去”。

賬號+密碼登錄
手機+密碼登錄
還沒有賬號?
立即注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