堅守中有新解——評李舫的散文
散文是最古老的文體,也是不斷煥發新生機的文體。特別是一些中青年作家,近年來他們的散文呈現出的新樣貌,預示了這個古老文體無限的可能性。其中,李舫就是一位成就突出引人矚目的散文作家。李舫是個女性作家,但讀她的散文,卻有一種不讓須眉的丈夫氣,一種氣貫長虹的浩然之氣。她的散文,按照批評界慣用的說法,多為“宏大敘事”。“宏大敘事”是一個具有極大內涵的概念,有的評論家曾經批評那種大而無當、空洞浮泛沒有內容的作品為“宏大敘事”,其實不然。真正意義上的“宏大敘事”——那種具有家國情懷、有內容、有擔當的作品,理應得到重視和肯定。李舫的散文,就是我所看重的那種“宏大敘事”,雄渾沉潛,雄邁大氣。只要看她的題目諸如:《茍利國家生死以》《春秋時代的春與秋》《千古斯文道場》《在火中生蓮》《紙上乾坤》等,就知道李舫在書寫什么,在關注什么。她寫的人與事,對中華民族是“鑄魂”的人與事,是確立中華民族元記憶的人與事。延續偉大的民族傳統,鑄造民族恒久不滅的靈魂,是這些篇章最初的動因和基本思想。因此,這樣的宏大敘事通過文學化的表達,我們就如同面對長江黃河泰山昆侖,心中升騰起的是敬意、尊崇以及闊大無邊的情懷和向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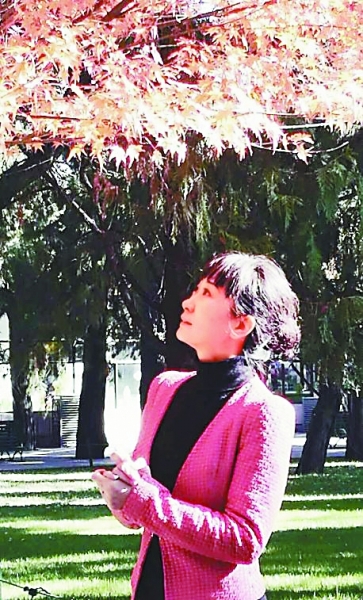
李舫近影
李舫的散文取資范圍相對集中、影響較大的作品,幾乎都與歷史有關。歷史就是時間——“時間,也許更是一代宗師‘蒼繁柳密’的武林手段、‘風狂雨急’的江湖腳跟。在無數個刀鋒撲面而來,閃爍在令人窒息的時間碎片里。兒女情懷,時代風云,武林快意,在雨滴煙橫、雪落燈斜處,淡淡暈染。天下之大,一塊餅到底是一個武林還是一個世界,其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作為一個人,不論居廟堂之高還是處江湖之遠而心憂天下的情思。”這是李舫矚目歷史——時間的原初想法。她意在告知我們,歷史已經遠去,時間不會倒流。但遠去并不是過去,歷史仍在今天揮發著巨大作用。于是,她縱橫于中國古代歷史立馬橫刀任意馳騁。從先秦諸子百家一直到大清王朝乃至當代,古今事,笑談間,她對史料的把握和文學性的處理,獨具匠心別具一格。她有一名篇《春秋時代的春與秋》,是專述孔子與老子的篇什。春秋時代是一個偉大的時代,錦繡瑰麗巨人輩出。它如詩如畫氣象萬千,又如遠在云端魅力無邊。那個時代,是我們民族的元話語時代,民族的思想瑰寶鉆石般地光耀千秋萬代。因為有了那樣的時代,中國文化才可以在世界民族之林中被尊重被敬慕——
在雅斯貝爾斯提到的古代文明中,有兩個中國文化巨人,一個是孔子,一個是老子。孔子專注文化典籍的整理與傳承,老子側重文化體系的創新和發展。一部《論語》,11705字,一部《道德經》,5284字,兩部經典,統共16989字,按今天的報紙排版,不過三個版面容量。然而,兩者所代表的相互交鋒又相互融合的價值取向,激蕩著中國文化延綿不絕、無限繁茂的多元和多樣。
李舫援引黑格爾的話說:“一個民族有一群仰望星空的人,他們才有希望。”而兩千五百年前的長夜里,老子與孔子就是兩位仰望星空的智者,他們剛剛結束一場人類歷史上的偉大對話,旋即堅定地奔向各自的未來——一個懷抱“至智”的譏誚,“絕圣棄智”“絕仁棄義”“絕巧棄利”;一個滿腹“至善”的溫良,惶惶不可終日,“累累若喪家之狗”。在那個風起云涌、命如草芥的時代,他們孜孜矻矻,奔突以求,終于用冷峻包藏了寬柔,從渺小拓展著宏闊,由卑微抵達至偉岸,正是因為有他們的秉燭探幽,才有了中國文化的縱橫捭闔、博大精深。
這是李舫的想象,也是李舫站在今天向偉大先賢的致敬;《千古斯文道場》,寫的是稷下學宮的流變。稷下學宮,又稱稷下之學,戰國時期田齊的官辦高等學府,始建于齊桓公田午。稷下學宮是世界上第一所由官方舉辦、私家主持的特殊形式的高等學府。中國學術思想史上這場不可多見、蔚為壯觀的“百家爭鳴”,是以齊國稷下學宮為中心展開的。它作為當時百家學術爭鳴的中心園地,有力地促成了天下學術爭鳴局面的形成。當然,那也可以看作是整個民族的啟蒙之學。這樣一段浪漫而偉大的歷史,為一個現代知識分子提供無限想象和馳騁的空間。于是李舫眼前出現了這樣一個歷史場景——
這樣一群人轟轟烈烈,銜命而出,他們用自己的智慧、立場、觀點、方法,去觀察,去思索,去判斷,他們帶來了人類文明的道道霞光,點燃了激情歲月的想象和期盼。當時,凡到稷下學宮的文人學者、知識分子,無論其學術派別、思想觀點、政治傾向,以及國別、年齡、資歷等如何,都可以自由發表自己的學術見解,從而使稷下學宮成為當時各學派薈萃的中心。這些學者們互相爭辯、詰難、吸收,成為真正體現春秋戰國“百家爭鳴”的典型。
當然,“稷下學宮薈萃了天下名流。稷下先生并非走馬蘭臺,你方唱罷我登場,爭鳴一番,批評一通,絕大多數先生學者耐得住寂寞,忍得住凄涼,靜心整理各家的言論。他們在稷山之側,合力書寫這本叫做‘社稷’的大書。”因此,與其說李舫在寫稷下之學,毋寧說她在面對當下。
李舫不僅關注本土歷史題材,西方歷史人物和事件,也是她選擇和表達的對象。墨西哥女畫家弗里達·卡羅、俄羅斯抽象主義畫家瓦西里·康定斯基、瑞士雕塑家賈柯梅蒂、挪威畫家愛華德·蒙克等。這些文章原則上可以稱作散文,這是相對韻文而言。但具體說來,它們也可以是人物傳記、片段藝術史或者其他什么。文體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李舫用她豐富的藝術史知識,以發現邊緣的執著,讓我們有機會看到了域外那些大藝術家卓然不群的風采和命運。她對人物藝術成就,尤其是命運的關注,給我留下極深的印象。她對這些為藝術帶來革命性變化、創造了新時代的巨匠,以敬仰、同情、惋惜、贊頌等豐富又復雜的筆觸,就這樣展現在我們面前。在豐富我們藝術史知識的同時,也喜憂參半地體會了別樣的人生。
修辭的豪放、雄邁,是李舫的散文一大特點。這自然與她個人性格、修養乃至趣味的選擇有關。比如在《大道兮低回——大宋王朝在景德元年》一文,是寫“命乖運舛的景德元年,宋真宗歷經天災、人禍、兵燹的考驗,審時度勢,終于在這年的臘月打開了一個叫做‘澶淵之盟’的錦囊,從此,大宋王朝開始了養精蓄銳、潛心發展的進程。”行文開篇卻是“繽紛的焰火,在除夕漆黑的夜空砰然炸裂,如流星雨一般飄然散落,帶著明亮的尾巴,劃出絕美的線條,遼闊而寂靜。”修辭雄健大開大闔,這是為文章“造勢”,也是奠定文章的基調。在這種驚天歷地的情勢中,預示了大宋王朝景德年間的多事之秋。因此,李舫的散文無論是說人說事,都有她整體的構思和設計。她熟悉歷史材料駕輕就熟信手拈來,但不是信筆由韁隨心所欲。她寫的是散文,文字灑脫自如,同時文章又包裹得很緊,須臾未離文章的“核兒”。她所有的文章幾乎都有這樣的特點。
另一方面,通過李舫的創作,也可以印證當下關于文學藝術論爭的某些觀點。這就是文學藝術變與不變、創新與守成的爭論。在文學藝術史上,古今之爭、新舊之爭一直在延續。變是絕對的,不變是相對的。但是,就文學藝術而言,堅持那些不變的觀念可能更難。面對一個大變革的時代,堅持不變、守成,就意味著守舊、保守、頑冥不化、九斤老太。但是,文學藝術的價值標準,包括對忠誠、正義、愛、友誼、善等的基本人性的要求,能變嗎?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關于文學藝術與物質生產的不平衡規律,已經闡明了這一點。我想,李舫對歷史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的專注和書寫,也可以理解為是對“舊”的堅守,但她有自己心的闡發和立場。這樣,堅守中有新解,創新不廢知常。她的創作便根深葉茂,既有歷史感又有當下性。李舫自己說:“我對于自己的定位,就是一個以筆為刀、為劍、為玫瑰、為火炬的作家。以一己之力,遙問蒼穹。而我對作家的定義,就是智慧和擔當,作家以筆、以命、以心、以愛、以思,鋪展歷史的長卷,謳歌生命的寬闊,時而悲愴低回,時而駐足仰望,在暗夜里期冀星辰,他們宛如子規長歌,恰似啼血東風,幽微中蠡窺宏闊,黯淡里喜見光明。……讀萬卷書,行萬里路。這是我的日常生活,也是我關乎大悲喜和大徹悟的哲學問道,其中的趣味和悠然,不言自明。”她對自己的期許令人感動,當然也令人羨慕。在李舫大作《紙上乾坤》出版之際,我對她的作品做了這樣的評論。我期待她取得更大的文學成就。
孟繁華(沈陽師范大學中國文化與文學研究所所長、教授)

賬號+密碼登錄
手機+密碼登錄
還沒有賬號?
立即注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