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途的“第四輩子”:《新工人》三部曲的生命見證
2008年,呂途告別了在歐洲的生活來到北京,她把這稱為她“第四輩子”:此后近十年,她訪談了上百名相熟或陌生的打工者,開辦并參與了八年工人大學的教學工作,還建設了34畝的“同心桃園”社會經濟組織,與此同時,記錄和探討打工者生活、文化與命運“中國新工人”三部曲陸續寫成,對呂途來說,她的“一生走了這么久,經歷了這么多,好像都是為了這第四輩子做準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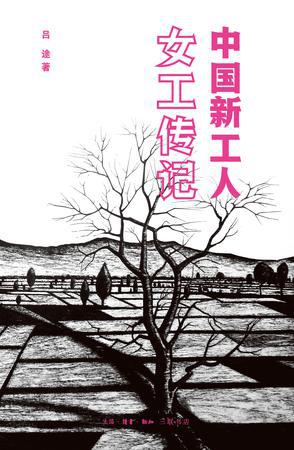
《中國新工人:女工傳記》圖書封面
今年11月,三部曲最后一部《中國新工人:女工傳記》終于出版。相比起此前《中國新工人:迷失與崛起》《中國新工人:文化與命運》兩部作品,《女工傳記》一書果斷而令人驚訝地切除了理論探討與材料分析的環節,而選擇直接呈現每位工人的生命故事。我們或許可以隱約理解呂途的用意:多年來,她的生活和命運與“新工人”這個標記下每一個活生生的個體日益緊密地綁結在一起,這些與她分享自己生命故事的人,早已不能被干癟地劃分到某種可歸類、可拆分或可數據化的“研究對象”,她的教學、研究或工作,也早已不再被設想為某種理論性、學究性并與鮮活的生命經驗相分離的“科學調查”。在與工人對話和交心的過程中,原本僅僅被視為研究環節或方法的“生命故事”越發顯現它自身的力量:呂途寫道,這本書將“是對生命本身的體會,是對生命力的歌頌”,她期望通過生命故事的分享激發讀者與書本中形形色色主人公的對話,也期望在生命故事的講述中,我們能夠看到生命力的閃爍火苗——那是一種對善良、公平、正義和尊嚴天性般的向往,也是新工人意識覺醒的希望印記。
12月16日,《中國新工人:女工傳記》新書發售會在海淀三聯韜奮書店舉辦。會議還邀請到活躍于皮村文學小組的張慧瑜、范雨素進行對談。九野樂隊主唱張玉(她的故事也收錄在《女工傳記》中)同樣到場,與聽眾分享新工人文化歌曲。
呂途,1968年生于吉林長春市,荷蘭瓦赫寧根大學發展社會學博士,2008年開始就職于北京工友之家。
“三部曲”的歷程:用生命去見證與創造
《迷失與崛起》:認清現實
2008年,在比利時開會的孫恒邀請呂途到工友之家機構工作,呂途吃驚地回復,“機構沒有洗澡的地方啊,每天晚上不洗澡怎么睡覺啊?我也不想上皮村的廁所,太臟了。也許等十年以后吧”。然而,說著“十年后”的她幾個月后便踏上了皮村的土地。
迎接她的自然是皮村糟糕的物質與生活條件:房屋破舊,居住空間狹小,冬天不得不生爐子燒煤取暖。這難以忍受的環境開始讓她困惑:同樣生活在這個地方的其他工人為何能接受如此艱苦的條件?他們對未來有什么指望?呂途采訪了近150名工人對居住狀態與未來發展的看法,結果發現:在被問到“如果在城市待不下去怎么辦?”時,大部分人選擇“回老家”,但在被問到“對未來有什么打算?”時,卻有近90%的人堅持“在城市打拼”。
打工者在這份調查中呈現出的“過客心態”深深觸動了呂途:對他們來說,自己不過是這個城市的“過客”,而支撐他們忍受困苦的是那個遙遠的、可以回得去的家。一方面,她為這種“過客心態”憂慮——這種心態,讓他們對自己受到的壓迫更易選擇逆來順受,也讓他們放棄去爭取很多本應獲得的權利;另一方面,她對這種心態背后的愿望產生了懷疑——在農村普遍衰敗的今天,真的還有一個可以回去的家嗎?
對呂途來說,“中國新工人”三部曲中的第一部是一部“認清現實”之作:這些城市內的匆匆過客,到底面臨怎樣的現實?她結合既有研究數據,試圖通過微觀的工友的生命故事總結出的社會宏觀的結構樣貌,而呈現在她眼前的,是一種普遍的迷失:待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農村,以及迷失在城鄉之間的工人群體。
《文化與命運》:認識自己
事實上,在第一部《迷失與崛起》撰寫的大部分時間中,呂途都被一種深深的無力感籠罩。在一次蘇州的讀書會討論中,面對呂途對工廠或資本制度的種種批評,工友們卻顯現出極大的困惑:“我覺得社會很公平啊”,“哪怕不公平,至少也合理吧”,“哪怕有些不合理,至少很正常啊”。這些“公平”“合理”“正常”讓呂途感到,問題不僅僅是新工人本身面臨的嚴峻狀況,還有他們對這種狀況的默認或不自知。更令她失落的是,大多數工人顯然對自己目前枯燥難熬的打工生活是不滿意的,但在被問及未來愿望時,他們往往表示“我不想打工,我想當老板”——對他們來說,改變命運,就是要成為那個剝削自己的人來剝削他人。新工人們臣服于資本的邏輯,他們一面受到資本的壓迫,一面又將這種壓迫內化并認同了,他們既難以改變自己,也無法改變他人的命運。
這推動呂途去關注“文化”。什么是文化?我們來到“新工人三部曲”第二部的主題:文化與命運。文化是人的文化,是人對生活在此時此地的整體生活方式的體驗。在呂途看來,只有通過分析統治工人生活與視野的文化本質——換言之,只有認識自己,認識我們的工作、生活,我們希望或應該做什么樣的人,我們才能發現其根本困境以找尋解放道路。
有趣的是,相比起《迷途與崛起》歸納式的研究方式,《文化與命運》卻不急不緩地講述起一個個故事來。在這本書中,呂途更進一步走進新工人的生命歷程,開始關注他們曲折的經歷與細膩的情感——她看到,工人在生活與工作中表現出躁動、不安、希望等“情感結構”并非無中生有,它們內嵌在工人所處的時代背景和社會結構中;也正是這些復雜感受讓我們窺見文化在日常、在社會中的體現。呂途談到,《文化與命運》一書的主題,便是通過回顧生命故事,展現資本的邏輯是如何將人們牢牢抓住并加以內化的;在文化分析的過程中,它將矛頭鮮明地指向資本文化,指向新工人對這種文化的內化及其思想價值觀的斷裂。
事實上,在撰寫本書過程中,呂途也曾到蘇州的臺資廠做過流水線的女工。這短暫的打工經歷卻給她帶來深刻而黑暗的記憶。長時間的流水線工作讓她感到“自己沒有價值”,而工廠內盛行著當地工人對外地工人的欺凌,老工人對新工人的欺凌更讓她感嘆壓迫內化的嚴重性。在一種極端壓抑的氣氛中,“我變得沉默,老實,難以看到任何改變的希望”。
那么出路究竟在何方?
《女工傳記》:尋找出路
在《文化與命運》的寫作過程中,呂途的信念越發清晰:擒獲工人是資本的文化,資本和人/勞動者的對立正是我們所處世界的主要矛盾;反抗和解放的希望需要在一種新的、屬于新工人的文化中孕育,這意味著,我們將使文化成為“一種整體斗爭的方式”,通過文化批判、文化實踐來促進建立新工人個人和群體的主體性。
呂途將三部曲最后一部《女工傳記》視為“尋找出路”之作。這部作品特別地將目光投向“中國女工”:從50后到90后,她們的戀愛、婚姻和生育經歷,她們承擔的家庭責任和社會偏見,她們作為勞動者的生活,她們是否、又如何獲得解放與新生。在書中,呂途不再給出任何理論分析或理論建議,而是純粹地呈現生命故事。
1974年出生的輝蘭。在聽聞工廠一個被解雇的大學生曾逼著廠里把社保補齊才離開后,同樣打算離開工廠的她也開始爭取社保補繳。輝蘭接連在工廠,勞動局,政府信訪部分奔波,同時爭取到了1200多名女工的簽名與工廠談判,“第一次和領導平起平坐地走進會議室”,讓作為女工代表的輝蘭前所未有地自豪。圖為輝蘭夫婦在出租屋陽臺上一起做飯。(圖片來源:《中國新工人:女工傳記》)
1985年出生的段玉。她曾并不認為自己成長過程中受到過性別歧視,但人生中兩件事讓她極大地體會到了女性的痛苦:一是被媽媽逼婚,二是生完孩子成為家庭主婦時。段玉說起自己對女權的理解:“女性受到束縛,也會給男性帶來壓迫。”如今但她通過樂隊開始直接參加女工的活動,并在歌曲中倡導性別平等。
在呂途看來,文化的斗爭是一個群體的斗爭,也是每一個個體的斗爭,是每一個個體在自身命運和社會歷史的互動下,看清現實并找到自己的斗爭。從《迷失與崛起》《文化與命運》到《女工傳記》,她越來越傾向靠近個體,并傳遞生命本身的力量,“我希望了解更多人的故事,想看看更多人的生命力是如何伸展的”。個體的生命經驗有時單薄、無助,卻依然包含哪怕是一瞬間改變與抗爭的希望,呂途想要展現的,正是從歷史中走來,在現實中孕育的女工們的力量,是在這些個體生命經驗的匯集之中,女工群體堅韌的精神面貌。
對談:工人無力嗎?工人會覺醒嗎?
在對談環節,范雨素、張慧瑜就本書和新工人文化與呂途展開了探討。張慧瑜首先肯定了這本書對普通人、普通勞動者的關注。他同時指出,相比起成為某個群體的代言人,呂途更像一位傾聽者和對話者。作為皮村文學小組的一員,張慧瑜分享了自己在鼓勵并閱讀小組成員書寫的自己故事的感受:在典型的左翼文化書寫方式中,工人,尤其是女工往往被塑造成一種苦難的、憤怒的形象。但新工人的故事讓我們看到,憤怒的情感恰恰是最少的,這些工人有苦難,但更有對生命中苦難的一種堅韌和坦然,而每個個體故事的背后,都包含特定時代相似階層的人的痕跡。
范雨素則從自身感受對呂途《女工傳記》中的工人形象提出疑問。在她看來,這些書里的主人公呈現的并非女工的全景,而往往是其中的佼佼者——主人公多為50年代后的國企工人,或70年代后的維權代表與公益組織參與者。“用知識分子的話來說,這些人是覺醒者,他們展現的更多是一種正面的力量——但這恰恰跟跟我知道的工人故事并不相同。”更讓范雨素感到親近的是夏衍《包身工》與鄭小瓊《女工記》中的工人形象:這兩部作品相差了近百年,其中工人的遭遇卻依然如此相似,“這才是女工的真實鏡子——無力的、悲涼的女工。”
范雨素談到了讓自己感觸最深的一種無力處境:許多母親們與子女分別來城市打工,她們長期工作不敢辭職,長期忍受著不能與孩子見面的“挖心挖肺的煎熬”,但這以親情為代價來供養孩子上學的努力卻可能只換來一個“大學畢業等于零”。母親為了孩子的未來而放棄親情,但在巨大的付出下,孩子卻未必能獲得未來。我們這些人究竟該何去何從?范雨素如此發問。
呂途承認,《女工傳記》中的主人公不足以展現女工的全景。但即使是一個個例,也同樣帶有時代的痕跡,她們的故事是生命歷程和社會歷程的交織。呂途同樣提問:這些站出來的,嘗試去維護自己權利的女工真的特殊嗎?對大多數維權的女工來說,維權的經歷可能持續一年或短短一月,在此前的漫漫人生中,她們與其他工人一樣,都是流水線上沉默的工作者。那短短一年或一個月成為她們生命中閃光的日子,而踏出這一步的契機并不多么難尋:或許是生育,或許是受到其他女工的鼓舞,或許是聽聞此前某位大學生的行動事跡——它可能就發生在日常生活中某個偶然的、平凡的瞬間。“這些人真的特殊嗎?覺醒者和不覺醒者真的有天壤之別嗎?覺醒就那么難嗎?女工可能是無力的,但我也是時常無力的,那些所謂中產階級在面對房價、霧霾時也時常無力的。在工廠那樣困苦的環境下她們仍然可以活下去,我相信她們仍然具有力量。”
而面對“我們和我們的下一代何處去”的疑問,呂途則分享了自己在工人大學培訓中心的感受。工人大學前15期學員大部分是留守兒童,呂途認為,“當一個孩子思想精神處于巨大問題,也即,他們不知道為什么而學,覺得未來沒有出路、再有學習能力也沒有用的時候,往往迷失方向,也難以在學業上真正有所進展——光教知識是不夠的,還需要讓他們心理健康起來”。培訓中心設立了一個成長小組,讓兒童們分享各自的心理故事,而在課程講授上也盡量引導孩子從個案、從身邊現實出發思考該怎么辦、自己能做什么。在呂途看來,重要的是讓年輕的新工人們能夠在認清自己的基礎上找尋出路。

賬號+密碼登錄
手機+密碼登錄
還沒有賬號?
立即注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