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名人是如何積累資料的?
“水深則所載者重,土厚則所植者番”。古今中外大凡知識厚實、成果卓著者,無不在資料積累上下過苦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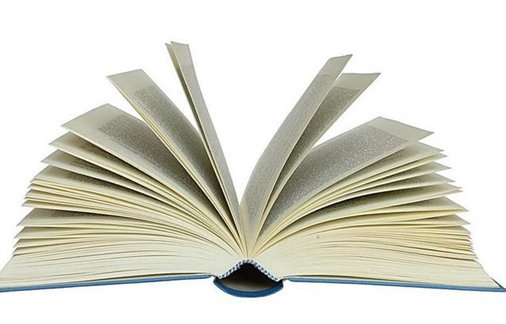
達爾文寫出《物種起源》這部劃時代著作,就得益于他所積累的報刊上的文章,甚至廣告、標題也成了他寫作的參考資料;魯迅為了完成《中國小說史略》,從1500多卷古籍中尋找所需求的資料,他說他是“廢寢輟食,銳意窮搜”;吳晗說過:“從來沒有一個做研究工作有成績的人不是搞資料工作的!”吳晗本人就有成套的卡片,為他個人治學發揮了巨大作用;法拉比、鄧拓等名人事業之要訣,也是成功地積累和運用資料。被人們稱為資料收藏家的鄧拓,把每天剪報比喻農民到野地提著筐子拾糞,從不空手回家。《人民日報》社的圖書館,完全是當年鄧拓重視資料收藏的結果。他說:“馬克思在許多專門學問上的偉大成就,正是以他的廣博知識為基礎的。舊時代的知名學者,程度不等地都可以說是雜家。”他像蜜蜂博采廣集,因而聯想豐富,后來產生了《燕山夜話》這部令人稱道的杰作。
有人將資料積累和調查研究等量齊觀。艾豐寫的《水,讓我們重新認識您》,之所以比別的宣傳節水文章具有深度與可讀性,與他靈活運用了地理知識不無關系。穆青說:“我寫《維也納的旋律》就翻了許多音樂方面的資料。從這篇報道上看,我是很懂音樂的。實際上我只是一個學習積累的過程。沒有理論和歷史文學方面的廣泛知識,像《歷史的審判》這樣的報道是寫不出來的。知識的基礎非常重要,有許多新聞,加上一點背景資料,馬上就活了,意義就深了。”有些資料的積累是臨時逼出來的,逼出來就要珍重愛護它,及時納入自己的資料庫,不要隨意散失。
積累資料功在長年累月,而利在一朝一夕,它的作用往往不是立竿見影、一勞永逸的。有的昨天才收集的,今天就碰巧用上了;有的存了十年、幾十年或許仍是“呆滯商品”;有的乃至以后一直用不上;有的是臨時性的,用了一次后就再也沒用了;有的是基礎性的,一旦儲存起來,可反復使用。不管是臨時性的還是基礎性的,只要跟寫作有關的,我們都要注意收集,積跬步,匯細流,持之以恒。

資料積累的方式各人有所不同,歸納起來不外乎以下幾種:
魯迅式:從文獻中收集,從書本中一字一句地抄錄。
蒲松齡式:向民間索取。蒲松齡為了寫《聊齋志異》,在路旁設攤聽過往行人講“鬼狐”故事。
達爾文式:向大自然索取。達爾文除了積累報刊文章,主要是靠漂洋過海、四方漫游,考察和研究各種生物遺骸中積累大量活資料。
李賀式:隨見隨得隨記。他郊游見到別致的景物,就浮想聯翩,抒情吟誦,并隨手記下裝入口袋,回屋整理,琢成佳篇。
不論用何種方式收集資料,都得有一種最佳的資料載體。從含義上說要有特定性,限于對自己寫作有參考價值的東西;從內容上說要有廣泛性,社會科學、自然科學、人文歷史無所不及;從來源上說要有多渠道,,報刊文獻、民間傳說、地方史志均是資料的來路。
需要注意這樣三個問題:
一是貴在堅持。要有“不斷豐富資料庫”意識,養成隨時隨地收集資料的好習慣。
二是勤于分類。分類應以便于查閱為前提,開始可分粗些,資料多了,再細分。
三是善于整理。資料整理有這么幾層含義:A、補充新資料;B、新資料取代老資料;C、糾正原資料中不準確的部分,防止引用時誤傳。
四是積極使用。積累資料不是裝潢門面,而是學以致用,有空經常閱讀資料,領悟寫作文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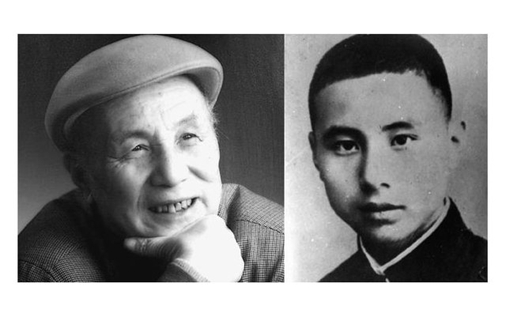
新華社原社長穆青在談及青年記者的修養時說:“一個記者的財富不是彩電、冰箱,而是看你有沒有豐富的知識積累、感情積累、思想積累,這種積累就像在銀行里存款一樣,存得越多,支付起來就越自如;沒有積蓄,遇到應急,借債都借不到。”古語云: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就是這個道理。運用資料,加強學習,腦勤筆勤手勤,做到“拳不離手,曲不離口”,天長日久,必能熟能生巧,通曉十八般武藝。

賬號+密碼登錄
手機+密碼登錄
還沒有賬號?
立即注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