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修文散文集《山河袈裟》:以修身來修文 以修文來修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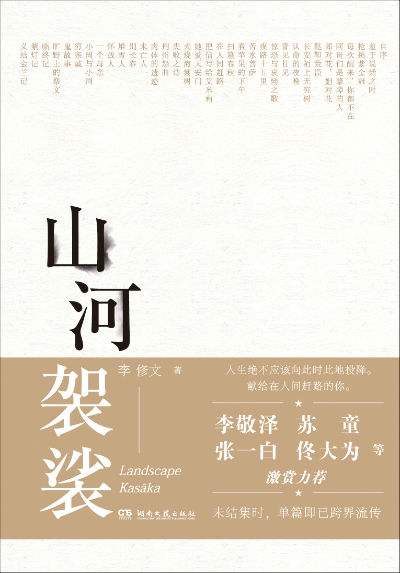
“李修文用十年的心靈史的碎片,反觀一切生活的人與事,通過自我反省體察,終于擁有了自己的精神封地:做人作文的‘山河’。于此,他與這個時代建立了獨特而有效的對話關系,在關注個體的同時為自己同代人找回歷史,找回作為一個文人的現在與未來。
在流行語言粗鄙化的當下文壇,《山河袈裟》中蒼涼而熱烈、豐瞻而俊美,既千回百轉又沉郁頓挫的文字,在體現漢語言之美的同時,更張揚了傳統的文人氣質與美學風格。”
《山河袈裟》是一部哽咽之著,一部令作者讀者心生哽咽之感的散文隨筆集。“哽咽之感”作為書中的關鍵詞,它每每出現在作者李修文與那些萍水相逢、身陷困境的人們面對面時,是他被這些苦難中的人性溫暖與重量感動時的情感狀態與寫作狀態,哽咽得一句一頓,簡樸瑣碎卻飽含深情,沉郁頓挫卻謙卑鄭重,顯示出深切動人的敘事力量;同時,這何嘗不也是讀者我們的閱讀體驗,因為作者描述的就是我們的生存與精神狀態,字里行間的人物其實就是我們,以及我們的兄弟姐妹。
哽咽之感,其實源自李修文10年的沉潛與漂泊,源自他身心投入地以修身來修文,當然也以修文來修身。
以困頓修身找到
自己的精神封地
一方面以困頓修身。全書33篇文章,是李修文在普通人困頓的人生里拷問自我,拷問人間、拷問人性,以此實現自我救贖,包括自我修煉。是作者10年旅途左沖右突的心靈寫真與懺悔錄,以自省為袈裟為修身。這種自省,在精致利己主義者遍地的今天,既彌足珍貴,也很容易引發共鳴,我們何嘗不也是與李修文一樣一次次從荒漠逃到荒島(《韃靼荒漠》),以求精神的再造。
李修文較好地處理了山河與袈裟、形而下與形而上的關系。他以內省的目光去發現與表現那些失敗人生的微光,一個個失魂落魄的人們如何沒有倒下,是黑暗中的火光,燭照了他們在“一場人世,終究值得一過”的一點信念,因為有過點點滴滴的反抗,便有哭有淚也有笑有歌唱,當然這歌唱像《郎對花,姐對花》那位風塵中唱黃梅小調的剛烈的母親,像《韃靼荒漠》中15歲孤獨男孩的半夜歌號,像《火燒海棠樹》中那位絕望地唱了15年戲的失孤寡婦等等,這每一種歌唱都是唱自己的絕望與希望。一如作者說他是寫給自己看的,唱給自己聽的。他關切的是這些朝死而活的落魄者的絕路逢生,逢生不是現實生路,而是其中命定的福分和機緣:窮街陋巷里,清潔工認了母子,發廊女認了姐妹,裝卸工認了兄弟等等,這是一首首《失敗之詩》。李修文寫道:“讓日子蒙上光亮,讓玫瑰死而復生的,恰恰不是點翰林,不是打金枝,它不過是我們日復一日在苦挨的羸弱、無聊和庸碌。正是它們,組成了一場等待,在如此等待里駐足,才反而配得起談論那兩個字:指望。”于是,那份與國民劣根性同在的人性情義,成了令人哽咽的指望;即使欲哭無淚,也有了心靈的一點歡欣,再卑微的人物也有了尊嚴,一如病房的岳老師與7歲小病號。重病中的岳老師對于彼岸的未來早已無能為力,但陷于人生黑暗里一個教師的潛能卻讓她生活在此岸,在被折磨得滿頭白發的她,于無用處卻有了作為。當她把病房當做課堂為病童講學以后,“某種奇異的喜悅降臨了她,終年蒼白的臉容上竟然現出了一絲紅暈”。作者遇見了許多未知的人生,包括自己的哽咽,直面人生,為自己當下負責,這份自省的修為令人唏噓。而臨別時,一直背不出下句的病男孩,居然哽咽地吼出“長安陌上無窮樹,唯有垂楊管別離”。作為同病房陪護的作者“當我看見微光映照下的她,難以自禁的,身體里再度涌起了劇烈的哽咽之感:無論如何,這一場人世,終究值得一過”。因為岳老師短暫的發光發熱,這生的意義把《長安陌上無窮樹》的希望之絕望,絕望之希望的情境推向了堅韌向上,擇善而生的極致,這何嘗不是篇令人哽咽之作。
李修文用10年的心靈史的碎片,反觀一切生活的人與事,通過自我反省體察,終于擁有了自己的精神封地:做人作文的“山河”。于此,他與這個時代建立了獨特而有效的對話關系,在關注個體的同時為自己同代人找回歷史,找回作為一個文人的現在與未來。為自己錄下所見所聞所思,以修身來修文,以修文來修身,從而完成自我的精神再造。
修煉漢字之美
顯見人心與山河
因此,《山河袈裟》的另一方面,是作者李修文在精神再造的“山河”中修文,他說:“山河人間就是寫作本身”。全書是他獨特的文學視角與獨特的表達,這當然來自修文獨特的目光與白描功夫,以及對中國文人傳統的張揚,來自他“干凈而有重量”的文字。我們隨意翻開任何一篇都會讀到作者語不驚人誓不休的句子,這些句子來自于作者對人物世事的同情之理解與理解之同情,于是,滿紙有學養有出處。寫小周卻起筆于那個令張愛玲絕望的胡蘭成的小周(《小周與小周》),寫通仁義的老猴卻與水滸英雄宋公明互文,弗拉門戈之于卡門,包括民間戲曲如此種種;尤其敘事的文字語感則接續傳承著文人的敘事傳統,頗具民國文風。《義結金蘭記》通篇三國水滸英雄般的契若金蘭,眾人眼中的傻子心地善良,救了受傷的猴王“宋公明”之后,居然在人間演繹了一場震動方圓百里的人猴情緣,雖沒有備下烏牛白馬,也沒有焚香結拜,滴血認親,但猴王宋公明卻以一生證明了自己的天地情義。傻子家遇難,它及時雨般解救;傻子家斷糧,宋公明自搭猴班掙錢養家,打家劫舍是為傻子家送吃穿用戴;甚至傻子死后,它充當義父撫養傻子的女兒;直至病入膏肓,也要爬上那輛永遠的綠皮車,與義女及眾鄉親永別,以便到遠處有尊嚴地死去。漫長的歲月里,猴王宋公明以忠義才智、劍心俠骨而感天動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作者以情義之筆,記下了這曲獨特的人猴義結金蘭的好漢歌,“一似山河入夢,一似世間所有的美德上都載滿了桃花。”
惟此,作為孤兒的傻子女兒才有人生值得一過的歡欣,才有李敬澤所言:“俠士寶劍秋風,在孤絕處、荒寒處、窮愁困厄處見大悲喜和大莊重,見出讓生活值得過的電光石火。”如此終結全書,也見出《山河袈裟》的大氣磅礴,見出33篇文字的活力與重量。
還值得一提的是,曾以《滴淚痣》《捆綁上天堂》等多部小說成名的小說家李修文常常把自己的看家本領小說細節散文化,比如是誰火燒了海棠樹,“恐怕只有我一個人知道真相。真相是這樣的——后半夜一個瘦弱的中年男子,打虛空里來,打茫茫霧氣里來,一手拎著蛋炒飯,一手拎著锃亮的斧子,走進了醫院”,“他先是站著哭,再去蹲在墻角哭,又回到窗前哭,如此反反復復,直到淚水打濕了他手中的斧子,但這被淚水打濕的斧子并不能讓他上天入地,反而讓他看見了更深的無能:即使陰陽相隔,他的斧子也砍不去厄運、崩潰和近在眼前的滿身繃帶,他惟一能砍去的,無非是那棵院子里的海棠樹。”此刻,精確的細節描述中,與作者同處理解之同情中的讀者君,能做的無非也就是與虛空的男子共謀。同時,我們也深深被作者這些有血肉、有痛感、有情義的文字感動,一句一頓,既簡樸專注又飽含深情,既犀利透徹又撕心裂肺,還儒雅莊重,頗具重量與美感。
是的,作者在修煉漢字之美中,顯見人心的山河與地久天長,修文里修身。作者這份深切的目光,不僅關注世間普通人的日常,更專注于那些萍水相逢的窘境里人們的可親可敬,并于此發現美善。于是,起承轉合,字里行間,氣韻生動,神采飛揚。文字緊密瓷實,思想情感密度頗大。比如《一個母親》寫人間至情的母與子,每天奔波于竹籃打水一場空的母親,只為那個已不識自己的兒子有一天又認出自己是他母親,她每天都靠這微茫的希望支撐著,令人哀傷而感動;而寫父子情的《每次醒來,你都不在》,那個在墻上涂抹對兒子思念的落魄凄惶的老路。用筆的情由是作者對墻上這句涂鴉而興起,從蹲墻發現老路,及其老路日夜截然不同的雙面人,一動一靜的兩種性格,一波三折的,層次節奏明晰,萬千回轉中戛然而止,謎底凸顯:我們看到這個千變萬化惶惶然的漢子,內心卻有如此令人哽咽的深情。文章意境深沉,韻律婉轉。凡此種種。
為失敗者歌唱
當然,全書也不乏詩意飛揚的散文寫作,如西班牙弗拉門戈的舞者,她超越自我的狂野與哀愁,令人著迷。還有寫西北花兒、黃梅小調、唱戲唱曲,既專業深入又剛柔相濟,既時時詩詞歌賦又處處入情入心,既可誦可歌又抑揚頓挫,既撕心裂肺又蕩氣回腸。還有思想隨筆,縱橫古今中外,先賢哲人,從秦漢三國到瞿秋白,從西緒弗斯到莎樂美、阿赫瑪托娃、里爾克、布羅茨基等等,李修文在一篇一篇的文字里,一一為失敗者歌唱,因為“真正的失敗者,明暗難辨,陰陽不分,巴比倫好似長生殿”,哽咽之時,能言誰之敗?明知其不可為,偏要為之,這份激揚而低回的文字,依稀貫穿著作者血脈里的楚人風骨。《荊州怨曲》明明臨死不屈,義薄云天,何怨之有?
我以為,在流行語言粗鄙化的當下文壇,像李修文這樣33篇作品,每一篇都經得起推敲,都能撥動讀者心弦。這些蒼涼而熱烈、豐瞻而俊美,既千回百轉又沉郁頓挫的文字,在體現漢語言之美的同時,更張揚了傳統的文人氣質與美學風格。可謂近年散文創作的新收獲,也是一部具有文學史意義的散文佳著。
最后想說一句,李修文對于修身與修文,二者都做得漂亮。為此,我們看到作者坦誠珍重而彌足珍貴的文學態度。
■創作談
寫作是游方時的袈裟
□李修文

收錄在《山河袈裟》里的文字,大都手寫于10年來奔忙的途中,山林與小鎮、寺院與片場、小旅館與長途火車,以上種種,是為我的山河,在這些地方,我總是忍不住寫下它們,越寫就越愛寫,寫下它們既是本能,也是近在眼前的自我拯救。10年了,通過寫下它們,我總算徹底坐實了自己的命運:惟有寫作,既是困頓里的正信,也是游方時的袈裟。
10年之前,我以寫小說度日,未曾料到,某種不足為外人道的黑暗撲面而來,終使我陷入漫長的遲疑和停滯,我甚至懷疑自己再也無法寫作,但是,我也從未有一天停止過對寫作的渴望,既然已經畫地為牢,我便打算把牢底坐穿,到頭來,寫作也沒有將我扔下不管。
有一年,我在醫院陪護生病的親人,因為病房不能留宿,所以,每每到了晚上,我就要和其他的陪護者一起,四處尋找過夜的地方,開水房、注射室、天臺上、芭蕉樹下,以上諸地,我們全都留宿過,一個冬天的晚上,天降大雪,我和我的同伴們在天臺上的水塔邊苦熬了一個通宵,半夜里,在和同伴們一起被凍醒之后,我突然間就決定了一件事情:自此開始,我不僅要繼續寫作,而且,我應該用盡筆墨,去寫下我的同伴和他們的親人。
他們是誰?他們是門衛和小販,是修傘的和補鍋的,是快遞員和清潔工,是房產經紀和銷售代表,在許多時候,他們也是失敗,是窮愁病苦,我曾經以為我不是他們,但實際上,我從來就是他們。
就是這些人:病危的孩子每天半夜里偷偷溜出病房看月亮,囊中空空的陪護者們想盡了法子來互相救濟,被開除的房產經紀在地鐵里咽下了痛哭,郊區工廠的姑娘在機床與搭訕之間不知何從,由此及遠——一個母親花了10年時間等待發瘋的兒子蘇醒過來,另一個母親為了謀生將兒子藏在了見不得人的地方,在河南,一只猴子和他的恩人結為了兄弟,在黃河岸邊,走投無路的我,也被從天而降的兄弟送出了危難之境。
是的,人民,我一邊寫作,一邊在尋找和贊美這個久違的詞。就是這個詞,讓我重新做人,長出了新的筋骨和關節。
也有一些篇章,關于旅行和詩歌,關于戲曲和白日夢,在過去,我曾經以為可以依靠它們度過一生,隨之而來的又是對它們持續的厭倦,可是,當我的寫作陷入遲疑與停滯,真實的謀生成為近在眼前的遭遇,感謝它們,正是因為它們,我沒有成為一個更糟糕的人,它們提醒著我:人生絕不應該向此時此地舉手投降。
這篇簡短的文字,仍然寫于奔波的途中,此刻的車窗外,稻田綿延,稻浪起伏,但是,自有勞作者埋首其中,風吹草動絕不能令他們抬頭,剎那之間,我便感慨莫名,只得再一次感激寫作,感激寫作必將降臨在我的一生,只因為,眼前的稻浪,還有稻浪里的勞苦,正是我想要在余生里繼續膜拜的兩座神祗:人民與美。
(李修文,湖北省作協副主席)

賬號+密碼登錄
手機+密碼登錄
還沒有賬號?
立即注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