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燕《陟彼景山》:一流的學者都是“干活的人”
今年1月,戴燕教授將十幾年來所作的十一位中外學者訪談結集成書,以《陟彼景山》為題,由中華書局出版。戴燕在序言中解釋了書的題名,這是取自《詩經·商頌·殷武》中的句子:“陟彼景山,松柏丸丸。是斷是遷,方斫是虔。松桷有梴,旅楹有閑,寢成孔安。”意思是登上高山,看到那些粗壯挺直的松柏,將它們砍伐、搬運下來,建成宗廟,用于祭祀祖先。借用“陟彼景山”為題,是要表達學術上的傳承和對前輩學者的敬意。書中訪談的前輩學者,包括何兆武、李學勤、章培恒、王水照、裘錫圭、朱維錚、陸谷孫、張信剛、興膳宏、川合康三、金文京等先生。在戴燕看來,作為專業的學者,他們長期研究中國,關心中國,已經在各自的學術領域“勤勤懇懇做了很多事”,而盡管謹守學者的本分,甚少對公共事務發言,但他們其實都懷有很強的社會責任感和人文關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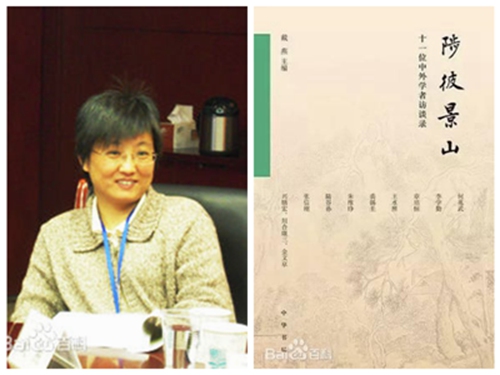
文匯報:《陟彼景山》這本書,收錄了11位學者的訪談錄,記錄了各人諸多學術經歷和思考。這些學者都有自己重要的著作、論文,讀者也可以通過他們自己的文章來了解其學術生涯,既然如此,為何還要做這一系列圍繞學術又不僅限于學術的訪談?
戴燕:本來不應該是我來拋頭露面,這就像紅娘搶了崔鶯鶯、張生的戲。我希望大家首先能明確一點:這本書的主角是書中11位我們很榮幸訪問到的前輩學者,我只是一個“跑龍套”的。
當然我也是經常在想,現在社會上老是在說要保護文化遺產,有物質的還有非物質的文化遺產,那么這些學者呢,他們做的工作甚至他們本人,難道不是重要的文化?是不是也應該得到保護?最起碼是給以記錄。
像何兆武先生,我們知道,他翻譯了那么多重要的西方經典。從1950年代起,他就翻譯盧梭,盧梭的不少作品都是他翻譯的,比如《社會契約論》。他還翻譯過康德、帕斯卡爾,后來又翻譯科林伍德等。這些肯定都是極為重要的文化成果。像陸谷孫先生,他是莎士比亞的研究者,他自己的研究、在課堂上講得最多的,大概是莎士比亞,但我們沒有聽過他講莎士比亞課的人,好多人肯定都用過他編的《英漢大詞典》《中華漢英大詞典》。這樣的字典和翻譯,在網絡的時代、全球化的時代,不知道以后是不是還需要人花那么多精力去編寫,可是但凡人做的工作,都不大有復制的可能,所以,何先生的翻譯、陸先生的字典,仍然是無可替代的,那里面有他們的精神。
在我們訪問過的這些學者中,何先生是年紀最大的一位,已經90多高齡了,其他先生,年紀最輕的,現在也已經退休。毫不夸張地說,他們經歷過的漫長時代,都已經成了歷史的一部分,他們出版的書和教學經歷,也凝結成了很珍貴的文化。
學者們平時在書齋里做他們的學問,時間寶貴,不大可能出來像明星一樣走秀。怎么才能讓更多的人了解這些學術研究者,讓社會上從事其他職業的人、年輕人知道學者的工作正是所謂“文化”的一部分,學者本身便是文化人?我恰好有一點機會來跑個龍套,因此便做了這些訪談,并將談話記錄下來,與大家分享。
我以前看胡頌平編寫的《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印象很深。他是胡適晚年的秘書,一天天記錄胡適的言談。在訪談錄里幾乎看不到他的存在,只有胡適的言行。我是佩服這樣的記錄者的,所以也要請大家千萬關注書中的那11位學者,重要的是他們,他們才是主角。
文匯報:書中的這些訪談,時間跨度很大,最早的是在上世紀90年代,最晚的應該是在2015年。這是對受訪者訪談記錄的一個回顧?
戴燕:這些訪談本來在不同雜志上發表,感謝中華書局我的老朋友,是他們建議我編為一集出版,讓我對自己多年的工作能有一個小結。
從第一篇訪談,到最后一篇,前后十來年。讓我有一點感傷的是,這里面,我訪問過的復旦大學章培恒、朱維錚、陸谷孫三位先生都已經先后離世。陸先生是在我看校樣時突然去世的,我跟他說出版社想要一張他的近照,印在書里面,他把照片傳給我,兩天后就走了。這幾位先生的談話,我們是再也沒有機會聽到了,但在這本書里,留下了他們對一些問題的看法,因此這本書的出版,也可以說是對他們的一個紀念。
老實說,我本來并不覺得我們對這些學者的訪談有多么重要,因為實際上是他們本人重要,而不是我們做的事情重要。但陸先生突然去世,多少改變了我的想法。學者們一旦離世,固然他們的學術研究成果還在,會轉為“文化遺產”,可是作為文化人的他們的個體卻不存在了。我們常說“文化”“文化”,說來說去有時候很空,其實文化應該是由這樣的個體構成的,學者們創造文化,也是文化的載體。所以,我愿意借這個機會呼吁,希望大家采取多一點方式來記錄我們的學者,保護這一類文化或說文化遺產。
文匯報:您訪談的對象大多是人文學科的學者?
戴燕:這大概與我自己的經歷有關,這些學者大多是我的老師輩。其中,李學勤、朱維錚先生是研究歷史的,王水照、章培恒、興膳宏先生是研究文學的,裘錫圭先生是研究古文字和歷史的,陸谷孫先生是研究英語文學和語言的,彭剛訪問的何兆武先生可以算是歷史和哲學吧。
比較特別的是張信剛先生,他是一位科學家,經歷也和其他幾位先生不同。他小時候跟父母從大陸到臺灣,后來到美國讀書,受的完全是西方式科學訓練,但他對中國文化始終有興趣。他在香港城市大學當校長時,我認識了他,他那時正在努力推動中國文化的教育和普及。在大學管理越來越趨向科學化的今天,有他這樣關心中國文化的校長是不是很難得?所以,我把對他的訪問也收在了這里。
雖然我訪問過的學者大多在文史領域,但是術業有專攻,他們真正的專業,也并非我能夠輕易進入,這本書記錄下的,應該說只是從一個角度對中國學界的一點觀察。如果要說有什么是一以貫之的話,那就是這十年思想人文學界的一些話題,在這里都有涉及,我們訪問過的學者都給出了答案。
文匯報:從您訪談的提問中,我們也能發現,這里面有一些您長期關注的問題,您也分別詢問過這些先生;從受訪者的回答也能看出,他們有一些共同的關懷。
戴燕:這些學者中,何兆武先生年紀最大,在他的《上學記》里,我們已經看到過有關西南聯大的回憶。其他各位基本上出生在抗戰前或抗戰期間,幾位中國學者,都是在1949年以后上大學,經歷過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風風雨雨,也經歷了1980年代的改革開放到今天。我做訪談時,當然會考慮他們各自的專業,提一些簡單的接近他們專業的問題,但實際上我比較關心的還是“世界觀”和“歷史觀”的問題。第一個世界觀,就是說從這樣的年代走過來,這些學者會是怎么樣看待世界、看待中國與世界的關系?
這些學者好像有一個共同點,他們大部分是在研究中國、關心中國,不用說,像李學勤先生和裘錫圭先生都是最頂尖的上古史專家,可有意思的是,李先生不但英文很好,他還曾學過俄語,早就有志于將中國古代和外國古代做一個比較性的研究。裘先生是研究古文字的,可是他也會用西方文化人類學的知識和理論來分析中國古代的思想。當然,像何兆武先生和陸谷孫先生是對西方文化比較有認識的,不過他們也算是中西兼通,何先生自己有英文版的《中國思想發展史》,陸先生對中國文化也有他獨到的見解,寫過很多這方面的文章和隨筆。
所以,我想從這些學者那里可以了解的,首先是他們對中國與世界關系的看法。我們知道,從五四以來,到后來的抗戰,中國思想界有一個很大的轉變,就是人們常說的“救亡壓倒啟蒙”。而這些學者基本上恰好是在“救亡壓倒一切”的這個階段念書受教育,形成他們對世界的看法,也就是對中國與中國以外的這個世界的看法,這就是我說的“世界觀”。所以在訪談時,我常常會問及他們對世界的看法,對當今諸如國學熱等有關社會思潮和話題的評價。
第二個是“歷史觀”。
這些學者大多從事文史方面的研究,對中國歷史、中國古代文化,當然有他們極為專業的研究和評價。但同時,他們經歷過的那些動蕩歲月、他們自己的經歷本身也已經成了歷史,成了中國現代史的一部分。因此在訪談時,我會注意到既請他們談他們的研究對象,也就是古代歷史,也請他們談他們經歷過的抗戰等歷史,這就是我說的“歷史觀”。而對這些問題,幾乎每一位學者也都有回答。
比如李學勤先生就說他1950年代上大學時,就對古代文明很感興趣,他有一個理想,是要將羅馬、埃及和中國早期的文明放在一起比較。這是一個比較史的觀念。這樣的理想,自然需要掌握多種外語才能實現,可是“文革”來了,外語學不成,他也不得不調整自己的方向。又比如說章培恒先生,他是深受魯迅以及五四新文化的影響,也曾見識過日本在侵華時期強迫人讀四書五經,因此對于如何繼承傳統、繼承什么樣的傳統,他就有自己的想法。
要說我在長達十年的訪談中,有什么一以貫之的問題的話,可以說就是世界觀和歷史觀這兩點。
文匯報:您在策劃這些訪談之前,是否對訪談對象有大致的選擇和標準?從書中可見,有些先生是比較愿意對公共問題、家國問題發聲的,而有幾位先生似乎更嚴肅低調一些?
戴燕:完全是機緣巧合,不曾有過完整的計劃,如果規劃過,也許不會是現在這個樣子。但書中的11位學者,大部分是我比較熟悉的,很榮幸得到他們的信任,愿意接受訪問,這是要萬分感謝的。過了這么些年,我也意識到,當時或許還是有一些潛在的標準。
首先,如果對中國的人文學界稍微有一點了解,就會知道我們訪問的這些學者,就他們在專業上的卓越成就以及影響力而言,都是公認的一流。正如有一位朋友說的,中國早期的歷史也就是夏商周的歷史,在今天能像這樣受到矚目,一個那么精深的專業竟然變成我們時代的顯學,李學勤先生絕對功不可沒,不管是他主持的頗受爭議的夏商周工程,還是他近年負責整理的清華簡,都是大家極為關心的話題。還有裘錫圭先生,他在四十年前已被稱作“文科陳景潤”,又是芝加哥大學的名譽博士,特別值得說明的是在他之前,中國的人文學者中,似乎只有胡適享受過這個榮譽。再有,像章培恒先生,他主編的《中國文學史》以及他提倡的將古代文學和現代文學打通的方法,也影響很大。朱維錚先生在近代史學界的地位頗高,因此晚年被授予德國漢堡大學名譽博士,最近十分暢銷的《哈佛中國史》的主編卜正民,在《哈佛中國史》的中文版總序言里還提到他曾受到朱先生的影響和鼓勵。日本的興膳宏先生主要研究中國六朝文學,他去年被選為日本學士院院士,這是他在日本學術界地位的一個證明,他的論著在中國有很多翻譯出版,上個世紀,他就在法國漢學界有了名聲。
其次,他們雖然大多是專業學者,謹守在學術范圍,并沒有對公共事務發言的習慣,但以我和他們長期交往的經驗,知道他們其實都懷著很強的社會責任感,有很強的人文關懷,對社會問題也有他們自己的意見,有的學者還非常敢于直言。這是要特別強調的。以前魯迅說陶淵明生當易代之際,沒有慷慨激昂的表示,于是博得“田園詩人”之名,但只要讀《述酒》一篇,就可知他于世事并沒有遺忘和冷淡。這一段常為人引用的話,我想正可以拿來形容我訪問過的學者,也就是說,他們都有超出專業的視野和心胸。
并不是說純粹的專業學者不夠好,可是如果少了這一層,訪談就沒有什么意義,讓讀者直接去讀他們的專業論文就好。
文匯報:從訪談里倒是可以看出這些先生大都很謙虛,他們已經在各自領域有了藏諸名山的成就,但在回答問題時還是常常談及對前輩學人的崇仰之情。
戴燕:你觀察得很對,真正好的學者,往往成就越高越是謙虛,不過更重要的是,我們常說的一流學者,應該還是俗話所說“干活的人”。
我看美國電影里面,還有講大數學家納什的《美麗心靈》、講大物理學家霍金的《萬物理論》,而在中國,以學者為主角的電影卻少之又少,不知道在其他職業的人眼里,學者的形象如何?是在象牙塔里,生活高雅而精致,還是像書呆子,缺乏常識、不近人情?我想說的是,就像普通的工人農民職員一樣,我們訪問過的這些學者,起碼都是整天干活的人。只要看看他們的學術成果,就可以明白這一點。比如何兆武先生,他翻譯過那么多書,還寫過那么多書,總有幾十種吧,然而我們也知道,他很謙虛,自稱“邊緣人”。就是在這樣的一生當中,他出版了那么多的書,靠的是什么呢,就是干活,就是出力氣。
陸谷孫先生晚年,學生們叫他“老神仙”。他還真不是什么神仙,就是個干活的人。他就住在學校附近,有時候我們去看他,看他為了編字典,書籍、材料攤一屋子,占據了吃飯桌。他每天就趴在那兒寫啊寫,既費腦力,也費體力,只有到了晚上才去學校散散步。
裘錫圭先生是我大學里的老師,“文革”剛結束時,他就在很小的一個宿舍里生活和工作,當時我們很多老師都是那樣,把床墊掀起來就當辦公桌,鋪下去就睡覺。前幾年他出版了六大卷文集,聽說是經他自己選擇過的,是他最重要的成果。那里面特別專業的文章我也讀不懂,不過放在手邊看一看,對他關心的問題、他的研究方法,還是會有一點印象,會知道他那些成果,必定是靠著長期艱苦的工作,一點一點積累起來,沒有捷徑可走。
王水照先生在宋代文學和文話的研究方面也有很大貢獻,我跟他在一個系里,每年一道參加研究生論文的開題和答辯,看見他對學生總是循循善誘、一絲不茍,便很能體會到他自律的習慣和踏實的作風。
我們可以了解,這些學者大概沒有一個人這輩子過得順風順水,都遇到過這樣那樣的坎坷、挫折,但就是這樣,他們還是做了那么多事情。可以想象,他們這一輩子該有多少時間是在研究、出版和教學,是在勤勤懇懇地干活。
文匯報:這些訪談集結起來一看,這些學者頗能反映一個時代的學術面貌。這一代人也有屬于這代人的獨特的經歷。您作為與他們接觸頻密的后輩學者,對他們的工作是否有一些個人的理解和觀感?
戴燕:我有時候也想,這些學者愿意為自己的工作付出幾乎全部,究竟是出于興趣還是出于責任心?這個問題,我沒有直接向他們去求證,不過我相信,遭遇這樣的時代和這樣的人生,很多事情是他們不曾想到的。何兆武先生翻譯的羅素《西方哲學史》很有名,1963年上卷初版,還不認識何先生的時候我就讀過,訪談中他提到,“文革”期間,他為此被關牛棚。所以說誰知道呢,你最初的興趣和理想,在后來會遇到怎樣的機緣和曲折。我更愿意相信,在這些學者身上,責任感是要大于最初的興趣的。
我自己是“77級”大學生,在“文革”結束后進大學中文系念書。我記得剛進學校時,聽系主任訓話,他說我們中文系不是要培養作家而是要教大家做文學研究的。可當時整個國家都處在一個歷史的轉折期,77級同學中大部分都有過務工務農的經歷,從社會上再回到學校,有些本來已是小有名氣的作家,所以雖然有這樣的系訓,但是同學中最早出名的仍然是一批作家和評論家,他們用自己的創作、評論參與到巨大的社會變革里面。我們那一代人,能夠進大學,就是因為有這場巨大的社會變革,參與其中,是很自然的事。
我訪問過的這些學者,正是我們的老師輩,當時他們也就四十來歲,也覺得“文革”結束了,終于可以做很多事,對未來充滿熱情。我年輕時就受這樣的老師鼓舞,直到現在也是。我們那一代人總覺得每個人的命運都是和國家的命運聯系在一起,好像不大會把純粹自己的興趣放在首位。我們也常常被老師提醒,中國有過那么長時間的“動亂”,學術也受到影響,就連對中國自己的古代歷史和古代文化的研究,有些方面甚至都比其他國家還落后。這對當時的我們是一個很大的刺激。
我們還是屬于有“落后就要挨打”的歷史記憶的一代人,所以總覺得我們的學習、研究,不是為了滿足自己的興趣愛好。這大概是我們這一代研究中國歷史、中國文學史的人都有的歷史包袱,不像現在的年輕人可以放平心態、自在一點,現在“中國崛起”了,在這個時代,不必要背那么大的歷史包袱。
文匯報: 盡管幾乎是同一代人,但不同的經歷也會使學者對中國文化的理解各有不同?
戴燕:不同學術背景的人,看問題的角度也會不一樣。比如張信剛先生,他有一點看法是我比較感興趣,也相當贊同的,就是說中國文化從古代發展到今天,毫無疑問,是世界上歷史最悠久、最光輝燦爛、文明程度也最高的一種文化,可是就像大家知道的,中國在近代被迫打開國門、面向世界,這樣也就有了各種新的問題,有些是傳統文化幫不了忙的問題。張信剛先生基于他自己的經歷提出一個問題來,他說中國要崛起,中國文化要得到世界的認可、要對世界有新的貢獻,中國文化本身是否需要更新?當然,類似的問題,也是我們訪問過的其他各位先生所關切的。
研究中國歷史、中國文化而不是簡單地沉溺于其中,能夠保持客觀的立場,是這些學者了不起的地方。他們仿佛有另一只眼睛,有很寬的視野,認為中國文化要繼續發展、要發揮更重要的作用,首先就要能夠自我更新。關于這一點,在三位日本學者那里可以看得更清楚。
文匯報:談談這本書的遺憾吧。還有哪幾位先前想過要訪問而最終沒有達成的?
戴燕:我自己感到最遺憾的,一位是金克木先生、一位是田余慶先生。
金先生晚年,有一段時間我跟他很熟,他和啟功、張中行先生合寫的《說八股》,就是我在中華書局時編的。那時我下了班會繞到他家里去坐一坐,陪他聊聊天,有時候我太忙或者覺得沒什么可說的,隔些天沒過去,他就打電話來。金先生有很多記者編輯朋友,知道各種消息,他也特別關心各種事情,每次見面都要提很多問題。我雖然不敢麻煩金先生,可他不知從哪里知道,還是會給我的文章提意見。金先生2000年去世時,我恰好在國外,突然接到他去世的消息,非常難過,因為再也沒有機會聽他談話、向他提問。
想對田余慶先生做訪問,是好幾年前就有的計劃,我也陸陸續續做了一些準備,主要是讀他歷年發表的文章。本來我們跟他住隔壁樓,也方便,可惜后來我到上海工作,離得太遠,總找不到合適的時間。2014年田先生也去世了,這就成了永遠的遺憾。
采訪/周語 整理/高矅

賬號+密碼登錄
手機+密碼登錄
還沒有賬號?
立即注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