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但得酒中趣,飲者留其名”的文狐

在中國二十世紀作家當中,活得最灑脫的恐怕就要數汪曾祺了,無論歷經時代興盛與衰敗,還是人生榮華與坎坷,他都是為自己人生的樂趣而活著。
■丁帆
老友金實秋囑我為他的新著《泡在酒里的老頭兒——汪曾祺酒事廣記》(廣陵書社出版)寫一個序,我欣然允諾,一是因為汪曾祺是我喜歡的一個有趣味的作家,二是因為此書專寫汪曾老的飲酒,我權當引吭高歌“飲酒詩”了。
在中國二十世紀作家當中,活得最灑脫的恐怕就要數汪曾祺了,無論歷經時代興盛與衰敗,還是人生榮華與坎坷,他都是為自己人生的樂趣而活著,一切皆是浮云,唯有醉在自我的生活之中,他才能把靈魂寄托在蕓蕓眾生的人生煩惱之上,只取人生快樂之飲。他并非魏晉文人與酒的關系,出世則是為了入世,汪曾祺的酒皆與出世與入世無關,酒是他的溫柔之鄉,汪曾祺是注定要活在酒鄉里的,他是無酒不成書的作家。亦如他說老人有三樂:“一曰喝酒,二曰穿破衣裳,三曰無事可做。”寧可數日無飯,不可一日無酒,當然下酒菜是要有的,所以為飲酒而做得一手好菜,這也許就是所謂酒仙的日子。
書中收集了許多汪曾祺飲酒的趣聞軼事,從中足可見出一個文人的心性,所謂酒品見人品,便是哲言。
家人說“有一次只剩老頭一人在家,半夜回家一看,老頭在衛生間里睡著了,滿屋酒味。”古諺道“一人不喝酒”,喝酒就是需要找一個傾訴對象進行宣泄的,所以,一般都是尋找與自己最密切的朋友喝酒,“酒逢知己千杯少,話不投機半句多。”而獨飲者卻只有三種人:一是酒精依賴者;二是孤傲者,三是前二者兼而有之者。汪曾祺是哪一種類型的飲酒者呢?讀者諸君從此書中自己尋覓答案吧。不過從其子汪朝在《我們的爸》中所言,即可看出汪曾祺在酒精作用下傾訴出來的來自血液中的孤傲:“葉兆言的一篇文章里談到,汪曾祺有一次跟高曉聲說,當今短篇小說作者里,只有你我二人了。我覺得這話還真像爸說的,尤其在酒后。爸是個很狂的人,自視甚高。不知其他作家是不是也這樣。他的文章里常引用一句古人的話:我與我周旋久,寧作我。他在外面還掖著點,在家里喝了酒有時大放厥詞,說中國作家他佩服的只有魯迅、沈從文、孫犁,意思是說,后面就是他自己了。”呵呵,這個溫柔心性的老爺子,酒后吐真言了,讓那些只從字里行間去分析汪曾祺的書呆子們大跌眼鏡。文人相輕,乃文人本性,只有在酒后才與外人言:“2004年3月的一天,黃昏雨后,在永嘉一個碼頭邊,酒后耳熱,林斤瀾說汪曾祺看不起王蒙,看不起王蒙的文章,也看不起王蒙的做官……趁著這個話題,我忽然問:‘我看你也不會在汪曾祺的眼里。’林斤瀾哈哈笑道:‘當然,他酒喝多了還會說自己勝過老師沈從文了。’”(程紹國《林斤瀾說》,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年版)由此可見,文人酒里酒外的話孰真孰假,不言自明。
何以解愁,唯有杜康;何以快樂,只須劉伶。汪曾祺不是那種“醉里從為客,詩成覺有神”的靈動創作者,亦非“斗酒詩百篇”的浪漫主義作家,也不是那種“眼看人盡醉,何忍獨為醒”的“同情與憐憫”式的俠客,更不是那種“斗十千”后為“長風破浪”“濟滄海”理想主義者,他真的是那種“但得酒中趣,勿為醒者傳”的趣味文人,“花間一壺酒,獨酌無相親”才是他飲酒的人生態度,也許這才是一個文人酒徒的最高境界。有人稱他為酒仙,無可不可,但這個仙不是指酒量,而是指那種喝酒的境界。葉兆言曾經和我談起過汪曾祺的酒量不過爾爾,但是他每天要飲最相思的此物。
做一個有趣的飲者,也許是汪曾祺喝酒的一種境界,這往往在他的文學作品中露出了蛛絲馬跡,小說《故鄉人·釣魚的醫生》寫道:“他搬了一把小竹椅,坐著。隨身帶著一個白泥小碳爐子,一口小鍋,提盒里蔥姜作料俱全,還有一瓶酒。……釣上來一條,刮刮鱗洗凈了,就手就放到鍋里。不大一會,魚就熟了。他就一邊吃魚,一邊喝酒,一邊甩鉤再釣。”說實話,這種飲者在中國的現實生活中少見,即便是在文學作品描寫中也是絕無僅有的,從中,我們可以見出先生對飲酒獨特性的激賞,以及他對文學作品趣味性描寫的美學追求。
然而,孤傲的飲者也是有酒中豪氣的。在小說《歲寒三友》中,靳彝甫請陶虎臣、王瘦吾在如意樓上喝過兩次酒。一次是他斗蟋蟀贏了四十塊錢,一次是為救兩位朋友度年關賣了被他視為性命的祖傳的三塊田黃,小說的結尾是這樣的:
靳彝甫約王瘦吾、陶虎臣到如意樓喝酒。他從內衣口袋里掏出兩封洋錢,外面裹著紅紙。一看就知道,一封是一百。他在兩位老友面前,各放了一封。
······
靳彝甫端起酒杯說:“咱們今天醉一次。”
那兩個都同意。
“好,醉一次!”
這天是臘月三十。這樣的時候,是不會有人上酒館喝酒的。如意樓空蕩蕩的,就只有這三個人。
外面,正下著大雪。
正如金實秋先生所言:“那臘月三十如意樓上的酒香在汪老心頭縈繞了四十多年,終于釀就了《歲寒三友》這篇小說,讓讀者分享了那‘醉一次’醇厚而悠長的馨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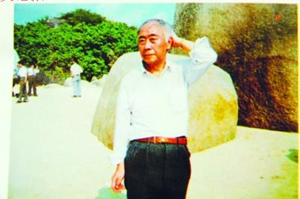
孤傲飲者是否也有借酒消愁的時刻呢?就讀西南聯大時,汪曾祺就是一個出了名的酒徒了,醉臥昆明街頭已經成為廣為流傳的軼事:“有一次我喝得爛醉,坐在路邊,他(指沈從文)以為是一個生病的難民,一看,是我!他和幾個同學把我架到宿舍里,灌了好些釅茶,我才清醒過來。”(《自報家門》,見《汪曾祺全集》第四卷)也許有人會詬病這種行徑:國難當頭,匹夫有責。作為一個知識分子應該擔當起抗敵宣傳的大任,豈能貪念杯中之物?但是,作為對抗日戰爭的一種無奈和失望,對于國家前途的擔憂卻無能為力,迫使他們端起了酒杯,這也是杯中之意。所以金實秋同時也從梅貽琦日記(1941-1946) 中尋找到了許多文人飲者的行跡,以此來證明當時知識分子的心態之一斑:
1941年7月18日中午,清華同學公宴,“飲大曲十余杯”,僅“微醉矣”;當月25日晚,赴飯約,“酒頗好,為主人(鄧敬康、王孟甫)及朱(佩弦)、李(幼椿)、宋等強飲約二十杯”,仍只“微有醉意”。1945年10月2日所記,他還很能喝“混酒”:“飲酒三種,雖稍多尚未醉”。長期出入酒場,難免也有辭酒誤事或失禮的。梅先生也不例外:1941年5月23日晚,清華校友十六七人聚會,“食時因腹中已餓,未得進食即為主人輪流勸酒,連飲二十杯,而酒質似非甚佳,漸覺暈醉矣。”以至耽誤了籌款的公事,“頗為愧悔”。同年12月6日又記,赴得云臺宴請,因先前“在省黨部飲升酒五六大杯,席未竟頹然醉矣,慚愧之至”。大醉之后,梅先生也曾發誓戒酒;1945年10月14日,晚上在昆明東月樓食燒鴨,所飲“羅絲釘”酒甚烈,“連飲過猛,約五六杯后竟醉矣,為人送歸家”,遂在日記中表示“以后應力戒,少飲”。而兩天后(17日),他又故態萌發,在日記中惋嘆:“(晚)約(楊)今甫來餐敘,惜到頗遲,未得多飲,酒則甚好。”
聞一多先生亦善飲,早在上世紀三十年代于國立青島大學(后改為山東大學)時即有酒名,時和楊振聲、梁實秋等人被戲稱為“酒中八仙”。浦江清先生亦是大飲者。今人錢定平曾于《浦江清日記》中發現,浦江清所記之“大宴小酌”竟有七十次之多。(錢定平《浦江清日記之境界》)。而一位名叫燕卜蓀的英籍教授亦是酒徒,極端不修邊幅而十分好酒貪杯。有一次酒后上床睡覺時,竟然把眼鏡放在皮鞋里了。第二天,一腳便踩碎了一片,只好帶著壞了的“半壁江山”去上課。(見趙毅衡《燕卜蓀:西南聯大的傳奇教授》,刊2004年11月10日《時代人物周報》)所有這些飲者的行狀,皆為抗戰時期的一部知識分子的心靈史。汪曾祺當然也是這一飲者隊伍中的一名更有故事的人了。所以金實秋把汪曾祺飲酒的文章與其他人的回憶收集在一起請諸君分享:
我有一天在積雨少住的早晨和德熙從聯大新校舍到蓮花池去……蓮花池邊有一條小街,有一個小酒店,我們走進去,要了一碟豬頭肉,半斤市酒(裝在上了綠釉的土瓷杯里),坐了下來。雨下大了。……我們走不了,就這樣一直坐到午后。四十年后,我還忘不了那天的情味,寫了一首詩:
蓮花池外少行人,
野店苔痕一寸深。
濁酒一杯天過午,
木香花濕雨沉沉。(見《昆明的雨》,載《汪曾祺全集》第四卷)
這是詩人情懷的汪曾祺。
“曾祺有過一次失戀,睡在房里兩天兩夜不起床。房東王老伯嚇壞了,以為曾祺失戀想不開了。正發愁時,德熙來了……德熙賣了自己的一本物理書,換了錢,把曾祺請到一家小飯館吃飯,還給曾祺要了酒。曾祺喝了酒,澆了愁,沒事了。”(何孔敬《長相思:朱德熙其人》,中華書局2007年版)
這是浪漫風情的汪曾祺。
“我在西南聯大時,時常斷頓,有時日高不起,擁被墜臥。朱德熙看我快到十一點鐘還不露面,便知道我午飯還沒有著落。于是挾一本英文字典,走進來,推推我:‘起來,起來,去吃飯!’到了文明街,出脫了字典,兩個人便可以吃一頓破酥包子或兩碗燜雞米線,還可以喝二兩酒。”(《讀廉價書》,見《汪曾祺全集》第四卷)
這是頹廢意緒的汪曾祺。
在昆明時,汪曾祺還在朱德熙家喝了一頓“馬拉松”式的酒。朱德熙的夫人何孔敬回憶說:“一年,汪曾祺夫婦到我們家過春節,什么菜也沒有,只有一只用面粉換來的雞。曾祺說:‘有雞就行了,還要什么菜!’我臨時現湊,炒了一盤黃豆,熬了一大碗白菜粉絲。我們很快就吃完了,德熙和曾祺還在聊天,喝酒、抽煙,弄得一屋子煙霧繚繞,他們這頓飯從中午吃到下午,真是馬拉松。”(見何孔敬《長相思:朱德熙其人》)
這是落魄文人的汪曾祺。
何兆武與汪曾祺曾住在一個宿舍里,彼此很熟,他說:“我宿舍有位同學,頭發留得很長,穿一件破布長衫,扣子只扣兩個,布鞋不提后跟,講笑話,抽煙,一副疏狂作派,這人是汪曾祺。”(劉文嘉《何兆武:如一根思想的蘆葦》載《人民日報海外版》2009年12月25日)
這是放浪不羈的汪曾祺。
一個一生以酒為伴的飲者,他的種種外在行狀都是從酒中呈現,而他的種種內心世界的思想也是在酒后的談吐中暴露。他應該知道其中的弊是大于利的道理的,但是你若讓他斷了這份念想,真是致命的。
斷酒如斷魂。
鄧友梅說:“從八十年代起,家人對他喝酒有了限制。他早上出門買菜就帶個杯子,買完才到酒店打二兩酒,站在一邊喝完再回家。”
關于汪曾祺是否因喝酒而死,我以為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們能否知曉一個作家與酒的血脈關系,陸文夫先生說出了一句振聾發聵的話:“文學豈能無酒?”“飲者留其名也有一點不那么好聽的名聲,說起來某人是喝酒喝死了的,汪曾祺也逃不脫這一點,有人說他是某次躬逢盛宴,飲酒稍多引發痼疾而亡。有人說不對,某次盛宴他沒有多喝。其實,多喝少喝都不是主要的,除非是汪曾祺能活百歲,要不然的話,他的死總是和酒有關系,豈止汪曾祺,酒仙之如李白,人家也要說他是喝酒喝死了的。”(陸文夫《做鬼亦陶然》,載《深巷里的琵琶聲——陸文夫散文百篇》,上海文藝出版社2005年版)
這不僅道出了汪曾祺一生與酒的關系,更說出了作家的性格決定了他文章的審美取向的真諦。
我們雖然不能說汪曾祺是一個高尚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但他可以稱得上是二十世紀酒趣和文趣皆備的作家。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我曾經為臺灣一家出版社編過一本汪曾祺關于美食文化的散文集,其中就說到:“從中,我們品嘗到了江南的文化氛圍,品嘗到了那清新的野趣,品嘗到了詩畫一般的人文景觀,品嘗到了人類對美食的執著追求中的歡愉。”“吃遍天下誰能敵,汪氏品味在前頭。”這也許就是對汪曾祺酒趣與食趣的最高評價了。
(丁帆:南京大學博士生導師。曾任南京大學中文系主任,文學院院長。現為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學會會長,中國當代文學研究學會副會長等)
附:
《泡在酒里的老頭兒——汪曾祺酒事廣記》
目 錄
序(丁帆)
題詞(王干)
前言
第一章:酒風余韻未曾衰
第二章:濁酒一杯天過午
第三章:解憂且進杯中物
第四章:衣上征塵雜酒痕
第五章:朋友來了有好酒
第六章:酒逢鄉親格外親
第七章:乘興揮毫一快事
第八章:酒仙醉臥愛荷華
第九章:無可奈何罷酒盅
第十章:偶爾輕狂又何妨
第十一章:不如且飲五糧液
第十二章:斷送一生唯有酒
第十三章:文章為命酒為魂
第十四章:唯有飲者留其名
附錄: 雜家金實秋 王干
《汪曾祺詩聯品讀》序 陸建華
《補說汪曾祺》序 葉櫓
《菰蒲深處說汪老》序 費振鐘
后記

賬號+密碼登錄
手機+密碼登錄
還沒有賬號?
立即注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