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從文九講》:連綴沈從文一生的蒙太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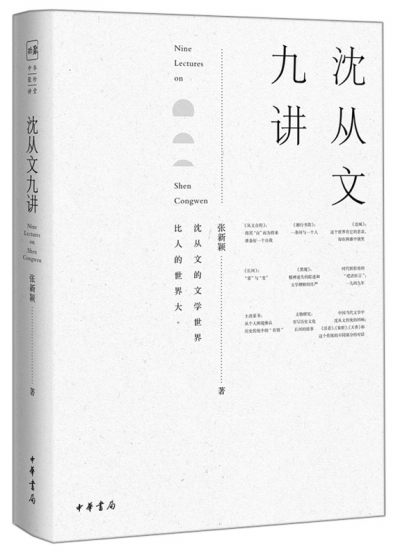
《沈從文九講》,張新穎著,中華書局2015年9月第一版,40.00元
《沈從文九講》沒有延續通常的文學史敘述,將沈從文簡化成書寫烏托邦式的中國鄉土、具有田園抒情詩人氣質的文學家,而是帶領讀者去了解作為文學家、思想者、實踐者的沈從文的一生,并將他的挫折、堅持與退守置于整個二十世紀中國的時空中加以理解。
理解沈從文,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沈從文去世后,妻子張兆和著手整理他的生前文字。這本該是借由文字和丈夫的一次重逢,意外地是,隨著越來越多的遺作被發掘,張兆和卻漸漸意識到自己過去從未真正理解丈夫。她在《從文家書》的后記中坦言:“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后來逐漸有了些理解,但是,真正懂得他的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壓,是在整理編選他遺稿的現在。過去不知道的,現在知道了;過去不明白的,現在明白了……越是從爛紙堆里翻到他越多的遺作,哪怕是零散的,有頭無尾的,有尾無頭的,就越覺斯人可貴。太晚了!”
在沈從文去世前一年,沈虎雛將謄寫好的《抽象的抒情》交給父親審閱。沈從文讀完后,卻感嘆“這才寫得好吶”——顯然,老人已經忘記了這篇文字。《抽象的抒情》是沈從文1961年在青島養病前后寫成的。那一年,他已經開始準備寫作《中國古代服飾研究》,一部無論對于他個人還是對于整個考古學界都意義重大的著作;而青島,則是湘西之外,沈從文最為留念的地方,因為他在那里度過“一生讀書消化力最強、工作最勤奮、想象力最豐富、創作力最旺盛”的三年,寫作了《從文自傳》《八駿圖》等作品,并開始醞釀代表作《邊城》。由此,不難推知這篇文章的分量。然而,二十多年后,八十五歲的沈從文已經將生命中這一重要的片斷遺忘了。
沈從文晚年有太多令人唏噓的片段,許多片段伴隨著老者的眼淚。整理家信時的眼淚,答記者問時的眼淚,聽聞老友離世時的眼淚。然而,比眼淚更讓人唏噓的是遺忘。也正是這次遺忘提示了我們一條為許多人忽視的理解沈從文的道路——“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認識‘人’”(《抽象的抒情》題記)。
復旦大學張新穎教授顯然留意到了這次遺忘。在新近出版的《沈從文九講》一書中,他將這條路徑概括成從沈從文理解沈從文。全書以此為基本方法,通過九個相對獨立的章節,講述了沈從文一生創作與實踐及其文學傳統在當代的回響。值得一提的是,該書的諸多篇幅也是張教授為本科生開設的“沈從文精讀”的課程講稿的底稿。作者以另辟蹊徑的方法、娓娓道來的講述、親近的文字,為普通讀者鋪就了一條“從沈從文來理解沈從文”的道路。
《沈從文九講》沒有延續通常的文學史敘述,將沈從文簡化成書寫烏托邦式的中國鄉土、具有田園抒情詩人氣質的文學家,而是帶領讀者去了解作為文學家、思想者、實踐者的沈從文的一生,并將他的挫折、堅持與退守置于整個二十世紀中國的時空中加以理解。作者把沈從文的一生分成三個階段:從一開始創作到1936年《從文小說習作選》的出版,是文學階段;從30年代中期到40年代結束,是從文學到思想的階段;1949年之后,一直到他去世,則是一個知識分子的實踐階段。三個階段分別對應文學家、思想者、實踐者三個形象,而“貫穿起這三個形象,大致上可以描畫出沈從文這樣一個比較特殊的人、比較特殊的知識分子,在20世紀中國巨大變動時代里的人生軌跡”。
又如,作者在分析沈從文在1949年后的文學創作時,沒有止于這些作品,而是通過與同時期的書信、檢討、自白等“并非有意識地當作文學而寫下的大量文字”的對照,得出后者“反倒保留了比同時期公開發表的文字創作更多的文學性”的結論。張新穎教授認為,“在特殊的社會、政治、文化環境下,文學作品的公開發表機制往往是意識形態審查和控制的方式”,對比公開發表的作品和書信,“我們會感受到一種堪稱巨大的反差,感受到書信所表露的思想、情感的‘私人性’與時代潮流之間的緊張關系。在特別時期,正是在‘私人性’的寫作空間里,‘私人性’的情感和思想才得以以文字的形式表達和存在,才保留了豐富的心靈消息”。可見,對沈從文而言,書信是一個特殊的私人寫作空間,不能簡單地說他的作家生涯到1949年就徹底結束。
分析沈從文土改時期的一封家信時,張新穎教授甚至直接援引同時期其他的書信來解讀信中夜讀《史記》的內容。這封信中關于《史記》的內容只有一千多字,但引用其他書信的文字大大超過了這個數字,并且全篇所有的征引文字都出于沈從文之手。篩選、剪裁、拼貼,無疑是簡單到極致的文字處理法,但張新穎教授直言,“在理解沈從文的所有方式中,從沈從文來理解沈從文是個基礎,就目前而言,這個基礎工作仍然沒有做好”。
“從沈從文來理解沈從文”雖說是“基礎工作”,卻對研究者有著極高的要求。在某種程度上,張新穎教授的角色近乎于剪輯師。如何從五百多萬字、三十二卷本的《沈從文全集》中“剪輯”出意味深長的生命片段,考驗的不僅是對文獻的熟悉程度,更是研究者的個人洞見。
張新穎教授敏銳地指出,許多讀者認為沈從文的景物描寫清澈透明,很“表面”,缺乏“深度”,但這種看似挑剔的“批評”其實道出了沈從文的“好”。他先從《湘行書簡》選取了這樣一段文字,“我就是個不想明白道理卻永遠為現象所傾心的人,我看一切,卻并不把那個社會價值攙加進去,估定我的愛憎……接近人生時我永遠是個藝術家的感情,卻絕不是所謂道德君子的感情”,繼而闡發出“‘深度’是‘焦點透視’產生的,要產生出‘深度’,一定要有‘定見’‘定位’‘定向’‘定范圍’,也就是說,一定要把‘眼光’所及的東西對象化,用‘眼光’去‘占有’景物,使景物屈從于‘眼光’,以便‘攫取’景物而產生出解釋的‘深度’。沈從文的‘看’,卻不是‘占有’式的,他(指沈從文)雖然未必達到莊子所說的‘使物自喜’的境界,卻也庶幾近之,因為有意無意間習得了‘至人無為,大圣不作,觀于天地之謂也’的觀物方式”。
而回溯《邊城》從醞釀到落筆的過程,作者更是將《從文自傳》中的渡筏,《新題記》《水云》《關于云南漆器及其他》中民國二十二年在青島遇見的為家人“報廟”的女孩,《湘行散記·老伴》中絨線鋪的女孩子等種種場景調度、連綴在三四頁的篇幅中,還原了《邊城》傳奇背后的一些本事。而這些經驗、記憶、情緒和思想的糾纏正是一位年輕作家的敏感心性的寫照。如此讀者更加理解作品中“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的無奈與悲哀。
或許,我們可以打一個不恰當的比喻,《沈從文九講》呈現了張新穎教授細心剪輯的九個生命片段,而這九個片段,連綴成作家一生的蒙太奇。將一部學術研究著作與電影畫面類比,似乎有些牽強。但耐人尋味的是,導演侯孝賢和賈樟柯都曾表示,自己的電影受益于沈從文的作品。這樣說來,蒙太奇的類比是有些道理的。《聶隱娘》那些風吹影動的空鏡頭,《小武》里那些偶然進入鏡頭的路人,和《沈從文九講》中“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的方法一樣,都是讀者對沈從文的文學傳統的回應。

賬號+密碼登錄
手機+密碼登錄
還沒有賬號?
立即注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