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云鄉:一個卓然特出的雜學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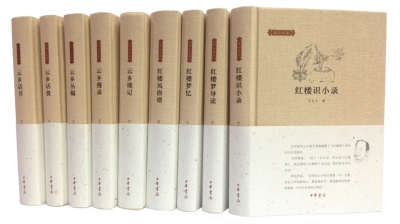
《鄧云鄉集》,中華書局2015年出版
“天下誰人不識君”,鄧云鄉先生便是一位名滿天下的士君子、文化人。鄧云鄉學名鄧云驤,生于1924年,故于1999年。鄧公出名較早,但出大名較晚,他原有紅學家之名,與魏紹昌、徐恭時、徐扶明并稱“上海紅學四老”,但鄧公在全國出名,還是在他出版了《魯迅與北京風土》一書之后。記得1982年此書剛出時,一位北京學者對我說,“從哪兒冒出個鄧云鄉,寫北京寫得這么好!”這本書是鄧公出大名的開始。我就是因讀了這本書,才知道了鄧云鄉的大名。之后,鄧公的著作一本接一本地出版,文章更是常見于各報刊,產量之高,真如中國紅學會會長馮其庸先生所評,“文章如泉源,不掘地而自出”。
粗略統計一下鄧云鄉的著作,計有《魯迅與北京風土》《燕京鄉土記》《文化古城舊事》《水流云在叢稿》《水流云在瑣語》《紅樓風俗譚》《紅樓夢憶》《紅樓識小錄》《紅樓夢導讀》《清代八股文》《云鄉漫錄》《云鄉瑣記》《云鄉話書》《云鄉話食》《宣南秉燭譚》《詩詞自話》《書情舊夢》《北京四合院》《花鳥蟲魚》《吾家祖屋》等近二十種。河北教育出版社為鄧云鄉出版了《鄧云鄉集》,最近中華書局增補重編后推出了新版。
人們讀鄧公的書,都知道他有學問,至有“滿腹學問,撐腸萬卷”之評,但要說鄧公算是哪一種學者,則說法不一。或說是民俗學家,或說紅學家,或說文史學家,或說北京史專家。是的,他確是這些方面的專門家,但還沒有說夠。鄧公還是掌故家、社會史家、散文家、詩詞家、書法家和美食家。讀了他的書便會知道,這些冠冕絕非浪得,而都是實至名歸的。這么多的“家”,我看可以用一個“家”來概括——“雜學家”。周汝昌先生曾稱鄧公的學問為“歷史雜學”。“雜”者,非蕪雜,博學之謂也,“雜學”乃博雜之學問,“家”是專家。“雜學家”者,學問廣博且專深之通人也。鄧云鄉正是一位在多個學術領域造詣精深的學問通人。
一、“晉籍上海人”的北京鄉愁
鄧云鄉原籍山西省靈丘縣,青少年時期在北京上學,畢業于北大中文系。新中國成立后在中央燃料工業部工作過一段,從1956年起在上海電力學院教書,至1993年退休。概括來說,鄧公可說是一位“晉籍上海人”,因他居京多年,也可說是一位準北京人。
鄧公是記錄和研究北京史地的大家。他的《魯迅與北京風土》《燕京鄉土記》《文化古城舊事》《宣南秉燭譚》《北京四合院》,都是可以傳世的力作。他對舊京歷史掌故的熟悉和精研程度,在很多方面超過了史上著名的北京史地專家張次溪、金受申等先生。特別讓人感慨的是,他一個“晉籍上海人”,對北京的鄉戀鄉愁,遠過于許多“生于斯長于斯”的北京土著。我是在北京長大的,“應知故鄉事”,但許多極有滋味的鄉土物事,我卻知之甚膚淺,只是在讀了鄧公文章后,才恍然知其妙處。
鄧公寫北京,從宮廷寫到市井,什么都能寫,什么都能寫得精細入微。比如寫北京四合院,他寫道:
四合院之好,在于它有房子、有院子、有大門、有房門。關上大門,自成一統;走出房門,頂天立地;四顧環繞,中間舒展;廊欄曲折,有露有藏。如果條件好,幾個四合院連在一起,那除去“合”之外,又多了一個“深”字。“庭院深深深幾許”,“一場愁夢酒醒時,斜陽卻照深深院”。(《書情舊夢》,東方出版社1996年版)
我自幼在北京四合院里居住,從未琢磨過這種住宅有什么好處,更不懂相關的建筑知識,只是渾然瞎住而已。看了鄧公對四合院的講說,才懂了一點四合院的妙處。
鄧公講說四合院的最精微之處,我認為是對四合院四時風韻的概括和鑒賞。他說,四合院是“冬情素淡而和暖,春夢渾沌而明麗,夏景爽潔而幽遠,秋心絢爛而雅韻”。(《書情舊夢》,東方出版社1996年版)這是多么精彩的描摹,不僅富有詩意,而且帶有哲理味兒。在鄧公眼里,四合院絕不僅僅只是一個居處,更是一種高雅精致的文化事象。比照鄧公所講,這四合院里的冬情、春夢、夏景、秋心,我都是經歷過的呀,今日回想,我真辜負了那美好的院落。
鄧云鄉是學者,他寫北京掌故,絕不像坊巷故老那樣,只是平擺浮擱地說舊事,而總是要尋出其源流和文化底蘊,使讀者建立起史的概念,獲得文化上的理解。比如,寫北京的名吃豆汁,他從京戲《金玉奴》別名《豆汁記》,講到古代文人墨客詠豆汁的詩,又講到古巷中賣豆汁的吆喝聲和唱豆汁的兒歌,既講歷史又說文化,使普普通通的豆汁與文化搭上界,使豆汁的掌故成為一種文化史料。
北京人的三冬“圍爐”,在常人看來似乎沒有什么講述的價值,鄧公卻重視這一中國北方古老的生活方式,他鉤索文獻,從方域特征、經濟生活、南人北遷等多個方面談“圍爐”,通過記述繆荃孫、李慈銘、魯迅等文化名人的圍爐軼話,勾畫出了舊京居民冬日圍爐的生活場景。
二、尋出《紅樓夢》后面的真史
在鄧云鄉的雜學中,紅學研究成績相當突出,“紅學家”名號在他的各種冠冕中也顯得尤為鮮亮。但鄧公之紅學不是“大路紅學”,他不研究曹雪芹的筆法和大觀園的階級斗爭之類。他的特點和特長,主要是善于尋出《紅樓夢》背后的真史,以幫助讀者從史的視角真正讀懂《紅樓夢》。我想這應是鄧公談紅的主要目的。
關于《紅樓夢》,他的主要著作是《紅樓風俗譚》《紅樓識小錄》《紅樓夢導讀》和《紅樓夢憶》。說是“風俗譚”“識小錄”,其實絕不只談風俗,也絕不限于“識小”,而是涉及多方面的歷史,政治史、制度史、經濟史、社會史、文化史等。既有微觀歷史,也有歷史大背景。
鄧公為尋出《紅樓夢》后面的真史,主要做了三方面工作。
一,給《紅樓夢》做史注,揭示文學描寫背后的真史或史的元素。這需要史家的功夫,鄧公深具這種功夫。《紅樓夢》多處寫到太監,如第十三回有“早有大明宮掌宮內監戴權”之句。鄧公認為這是“半今半古”的寫法。“大明宮”是唐代長安宮名,曹雪芹時代無此名,因為清廷絕不可能用“大明”作為本朝宮殿的名字。這是半古。清代有乾清宮、坤寧宮等,都是由太監管理的。這是半今。鄧公又解說了明清兩代的太監制度和區別,并指明《紅樓夢》時代的太監官品是以雍正元年為標準的。這樣,讀者便明了了紅樓文字背后的真史,也就自然把文學故事與歷史事實區分開了。
二,“以史解紅”,即用史實材料來解讀《紅樓夢》中的一些內容。賈寶玉的才學究竟如何?《紅樓夢》寫他在蘅蕪院辨認花草時引了《離騷》《文選》《吳都賦》《蜀都賦》等詩文,使眾人大為吃驚。就是說寶玉的才學十分了得。但鄧公列舉了《林則徐日記》和《邵二云先生年譜》中的史料,證明寶玉比起當時同齡的讀書種子來,還是有相當差距的。《紅樓夢》寫寶玉作詩時,竟忘了并不生僻的“綠蠟”一詞,遭到寶釵的嗤笑,便說明寶玉的學問還不到家。
三,發現《紅樓夢》事物的原型。“紅樓夢原型”諸問題,是紅學研究的重要課題之一,如推測大觀園的原型是北京恭王府之類。鄧公最先推斷“太虛幻境”也有原型,即北京朝陽門外的東岳廟。紅學家周汝昌在與鄧公的一次閑談時聽到這一推斷后為之一震,認為這一見解真是“石破天驚的奇言”。的確,若將東岳廟的牌坊、諸司、寢宮、侍女等設置與“太虛幻境”比照,確可以讓人感到東岳廟極可能就是曹雪芹構思“太虛幻境”的靈感之源。
鄧公既懂紅又懂史,在懂史這點上,他高于許多純文學出身的紅學家。他那些以史解紅的著作,實際可以作為紅學工具書來讀。正因為他在紅、史兩方面都有淵博的學問,所以他成了電視劇《紅樓夢》當之無愧的顧問。
三、掌故家兼社會史家
掌故是很有用的東西,研究歷史可作史料,文學創作可作素材,哲學、社會學可做案例……當個掌故家不容易,必須閱歷廣,博聞強記,掌故家可以說是歷史學家的偏師。好的掌故家須有史家素質,既要言之有物,更要言之有據。將掌故系統化,進行學理的研究,掌故家便成了社會史家。鄧云鄉便是一位極好的掌故家兼社會史家。鄭逸梅是掌故大王,徐凌霄徐一士兄弟被譽為掌故巨擘,我看鄧公絕不亞于他們,在不少方面還駕而上之,特別是鄧公已進到了社會史家的層次,更為鄭、徐所不及。
魯迅曾寫名文《關于太炎先生二三事》,其中提到章太炎的反袁氣節,因是雜文,不可能寫細節,這就需要掌故家來補說。鄧公有《太炎先生五題》一文,細寫了章太炎反袁氣節的掌故。他寫道:
袁世凱派他的二皇子袁克文,親自帶了錦緞被褥,送到龍泉寺。太炎先生在房中聽到外面有人聲,而且在窗戶縫中窺視,便撩起簾子一看,原來是袁抱存(克文字)送被褥。太炎先生想出妙法,跑到屋里,點燃一支香煙,把被褥一個、一個地燒了許多洞,扔在院中對袁克文說:拿走。這位“太子”碰了一鼻子灰只好去了。
這些掌故細節,在一般史書中是見不到的,鄧公把它寫出來了。這樣,一個特立獨行,有凜然氣節的章太炎先生,就站立在了我們面前。這段掌故實際是史料,可作為史學研究參考,若寫章太炎傳,或拍電影,更是不可多得的細節材料。
蔡鍔得到名妓小鳳仙之助,從京師返回云南,發動了反袁護國起義。這一段既嚴肅又風流的史事,被拍成電影《知音》,廣為人知。蔡鍔是怎樣逃離京城的?史書的記述皆大而化之,電影里也只是一兩個鏡頭。鄧公《蔡松坡之死》一文詳述了這段歷史掌故。其中寫道,在八大胡同頭等小班云吉班妓女小鳳仙的幫助下,在梁啟超所派的老傭人曹福的接引下,蔡鍔乘三等車到了天津,住進了日租界的同仁醫院,而后回到云南,宣布云南獨立,后又率兵進川,是為“護國起義”。
品讀這段細致的文字可以發現,“云吉班”“梁啟超派人”“曹福”“三等車”“日租界”“同仁醫院”,這些微觀史事信息,在一般談及蔡鍔起義的史書上是不易見到的。鄧公的記述起了拾遺補缺和存史的作用。梁啟超在護國起義中起到何種作用?蔡鍔當時與日本是怎樣的關系?鄧公講的這段掌故,可以作為研究這些問題的一種史料參考。
鄧公不只是記述掌故,也撰寫研究歷史掌故的社會史論文。如《中國葬禮的歷史演變》《清代物價三百年述略》《上海舊時地價與房租》《顏習齋與讀書無用論》《汪輝祖及其著述》等論文,都是他對零散的歷史掌故加以匯集、整理并進行學理性研究的結果。所以我說鄧公不僅是個掌故家,也是個社會史家。
四、為八股文說句公道話
清代以降,八股文的名聲逐漸變臭,最終被廢棄。清人徐靈胎諷刺八股文說:“讀書人,最不濟;濫時文,爛如泥。國家本為求才計,誰知變做了欺人技。三句承題,兩句破題。……辜負光陰,白日昏迷,就教騙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氣。”(清袁枚《隨園詩話》)全面否定了八股文。顧炎武說:“八股之害,甚于焚書。”更是恨透了八股文。
但八股文果真沒有一點好處嗎?鄧云鄉說,不,八股文也有它的可取之處,不然,它怎么能夠延續那么多年,而且明清兩代那么多英才都是八股出身呢?為研究八股文,鄧公研讀過八股文選集《眉園日課》,思考了多年,寫出了專著《清代八股文》,對八股文產生的制度原因、源流和歷史、文體特征、存廢爭議、與科考的關系、歷史作用等問題,都提出了精辟的見解。
他發現八股文是個利弊兼存的東西,弊在內容空洞無物,利在對訓練思維能力有用。他評說道:在八股文范圍和條件的嚴格限制下,人的思維能力的集中性、準確性、敏銳性、全面性和辯證性得到訓練,練出了這樣的思維能力,加上先天的聰明才智,再靈活地運用在實際上,“那便無往而不利,要詩要文,要明斷、要深思,要什么就是什么了”。(《紅樓風俗譚》之《曹雪芹·八股文》)這實際上解開了在八股取士之下也能產生人才的歷史之謎。《儒林外史》有句名言,說做好八股再寫詩文,便“一鞭一條痕,一摑一掌血”,我原來對這話不理解,但看了鄧公的論說便理解了。
對于八股文的弊端,鄧公也做了深入研究,《清代八股文》專設了《八股的歷史副作用》一節。
五、文筆雅雋的散文家
從運筆作文來說,鄧云鄉可說是一位文筆雅雋的散文家、隨筆家。明清史家謝國楨先生稱贊鄧公的文字風格為“雅雋”,我極以為是;然覺得還可加上“清俊”“蕭散”“醇美”“舉重若輕”“大俗大雅”等贊詞。
以雅雋之文字,道凡俗之物事,此為鄧公的絕大本事。一件俗事,一經鄧公雅雋文字的“點化”,便雅致可人。拿《燕京鄉土記》的標題來說,寫白云觀燕九節,標題作“燕九春風驢背多”,寫過年祭灶,標題是“黃羊祭灶年關到”,其他像“鞭影小騾車”,“消暑清供”,“秋風菜根香”等標題,都是雅雋非常的文字。又如禁城蛙叫,大俗事也,鄧公卻能聯想到晉惠帝聽宮蛙的笑話和古人“一池蛙唱,抵得半部鼓吹”的雅趣。北京初春的大風,在平庸寫手筆下,必是“呼呼地刮,迎來了春天”一類乏味無趣的文字,鄧公卻寫出了“大黃風一直吹到燕山腳下,吹開了凍土,吹發了草芽,吹醒了柳眼,吹笑了桃花,吹起了昆明湖的波濤,吹白了紫禁城的宮娥的鬢發……”這樣美麗的句子。
鄧云鄉是一位特別注意從古代美文中汲取養料的散文家。例如,他認為古人的許多日記雖是隨手札記,并未當作正宗文章著筆落墨,但文字卻很優美,其功力決不在宏文高唱之下。他寫有《日記文學叢談》一文詳論之。鄧公很喜歡清人俞樾的日記文字,在《讀俞曲園日記殘稿》一文中贊之曰“蕭散有致”“爐火純青”。我斷定鄧公有意向古人的日記文字學習過。多年來我讀鄧公文章,總覺得他像是隨隨便便寫的,但醇厚有味,不知是怎么弄的,后來才覺出可能是受過古人日記的影響。在鄧文的字里行間,好像能看到俞曲園的影子。
我還愿意把鄧公叫作文章家。因為他太懂做文章的門道了,他尤其擅長把散碎的材料組織成一大篇錦繡文章。《魯迅與北京風土》就是用散碎材料鑄成的大作品。此書以魯迅日記為經,以北京風土景物為緯,因人寓景,古今交匯,使魯迅和舊北京都“活”了起來。讀著這本書,仿佛看到魯迅先生又漫步在舊京的街巷里,故都的景物風情也盡收眼底。從文章學來說,這本書的架構和材料組織真是妙不可言。
六、讀書種子
讀鄧云鄉的書,常會冒出一個念頭:鄧公真是個讀書種子!讀書種子者,飽讀典籍文獻、能延續中華文化之大讀書人也。明代方孝孺、清代葉德輝都被稱為讀書種子,明成祖要殺方,姚廣孝諫曰不可,葉德輝是劣紳,革命黨要殺他,章太炎說殺不得,可見讀書種子之可貴。鄧云鄉也足可稱為讀書種子,名副其實,絕非虛譽。馮其庸先生曾問鄧云鄉,你怎么能寫那么多東西呀?鄧公答道:“天天寫,天天讀。”這“天天讀”三字,正是一個讀書種子的自況。
鄧公的居室,可謂書山亂疊,他每日就在這書山中讀啊,寫啊。從他著述的征引中,便可觀其讀書之多之雜,正史、野史、文集、筆記、雜鈔、縣志、日記、書信、游記、傳記、說部、詩詞、俗曲、俚諺、童謠,可謂無所不讀。他寫的文章之所以那么有血有肉,蓋因得益于讀書多,掌握的材料多。比如寫冰床,一般人只知道《帝京景物略》和《藤陰雜記》二書的記載,但他又引了鮮見的文獻《倚晴閣雜抄》和《水曹清暇錄》,這就使人對冰床歷史的了解更加細致,使讀者知道了原來在清代北京護城河里,還有以拉冰床作交通工具的生意和攜酒轟飲冰上的趣事。我很看重鄧公征引文獻的博雜,因為從目錄學上講,若記錄下這些文獻名目,便是一份很有用的書單。
鄧云鄉不僅讀書,還研究書。有道是“治學先治書”,鄧公深通此道。《舊都文物略》是一部北京史重典,湯用彬等編著,1935年出版。鄧公寫過一篇研究文章《舊都文物略小記》,把此書從編纂到出版的來龍去脈及重要價值,做了深入研究和詳盡闡釋。這部書成了他治北京史的重要工具。
《圓明園古籍二種》《清史稿瑣談》,也是他研究書的重要文章。《圓明園古籍二種》可謂一篇圓明園文獻的導讀,也是一篇圓明園史的研究文章,很有助于圓明園的研究工作。鄧公對清史非常熟悉,這與他熟讀《清史稿》分不開。他說自己的書架上總放著一部《清史稿》,寫清代文人歷史掌故時常翻閱此書。他一邊利用《清史稿》,一邊研究《清史稿》,多有心得之后,寫成了《清史稿瑣談》一文。
七、我與鄧云鄉的一點交往
我與鄧公有點交往,起于讀他的兩本書。因我大學曾寫過北京史論文,又素對魯迅文章感興趣,所以,一在書店見到他的《魯迅與北京風土》,便如逢故人,立即買下,并因此記住了鄧云鄉這個大名。后來又讀到了《燕京鄉土記》,當時光明日報正在全國搞書評征文,我寫了一篇評此書的文章,獲得了一等獎。估計鄧公看到了書評,因我曾聽人轉述,鄧公說,北京有個李喬,不錯。我與鄧公就這樣隔空相識了。
在北京日報,我編輯過文史版、讀書版,曾多次向鄧公約稿,我們的交往就多了,但主要是書信往來,只是在他擔任電視劇《紅樓夢》顧問時,我們在劇組駐地見過一面。印象是他太質樸了,不像民國老派學者那樣雍容,更沒有居高臨下的派頭,讓我驚異的是,他一個上海人怎么說京腔呢。后來我對鄧公的了解加深,崇敬也隨之增長,他的學問和人品成了我心中的一個典范。
我寫過三本社會史著作,《行業神崇拜——中國民眾造神史研究》《中國師爺小史》和《清代官場圖記》。追溯三書的寫作緣起,多少都受過一點鄧公著作的影響。尤其寫《中國師爺小史》時,他的《汪輝祖及其著述》一文對我有發蒙的作用。汪輝祖是清代名幕,他的史料是我研究清代師爺所需的最基本的史料之一。
鄧公的書齋名“水流云在軒”,取無爭、舒緩之意,類如陶淵明之“云無心以出岫”。鄧公做人,正派、平實、自然、不張揚、不自夸。我自覺多少受過一點鄧公人格的影響,或者自豪一點說,我與鄧公屬于同一類人。我有過升官的機會,但我舍不得書齋。鄧公,還有孫犁、黃裳等先生的書,對于我堅定一輩子穿長衫,不穿補服,有過楷范的作用。
鄧公的文稿是極易編輯的,因為幾乎無懈可擊,幾乎不用編。若改動也是因版面有限而刪節。鄧公有時寫得長了,不知能否全文發表,便在原稿上畫出可以刪節的地方,以使編輯既省事,又不為難怎么刪節。我還保存著這樣一篇手稿,每睹之,總會心生感動。
鄧公身上很有點民國文人氣,現在叫民國范兒。他寫信常用毛筆和花箋,還特制了一種自用箋,前端印“紅樓”二字,末端印“水流云在之室自用箋”。鄧公賀年,也沿襲舊俗老派。一次我逛潘家園,看到一張信紙大小的賀年片,毛筆書之,字跡圓潤秀勁,署名“晚鄧云驤”,有“水流云在之室”印。這無疑是鄧公之作,是寫給一位前輩先生的,我立即買了下來。以毛筆親書賀年片,這比時下流行的短信拜年不知要增重多少情誼。傳統文化的好東西,鄧公總是倍加愛惜并勉力行之。
余話
我贊成止庵先生的話,“世間再無鄧云鄉”。鄧公的本事,難學;鄧公的特殊價值,不可再生。有時我看到北京的某個文物被毀了,某條古巷消失了,就想,若是鄧公在,寫一篇關于這個文物、這條古巷的文章,登在報上,也許它們就保存下來了。但世間再無鄧云鄉了。惜哉!

賬號+密碼登錄
手機+密碼登錄
還沒有賬號?
立即注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