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問題的“經典”:古典?現代?后現代(馮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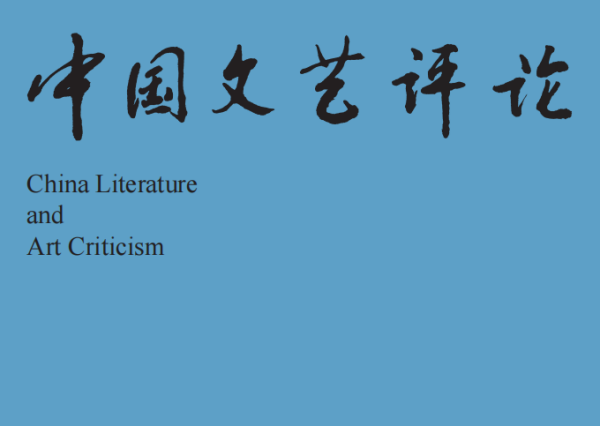
內容摘要:“經典”一詞的泛用已經成為常態。在中西方古典時期,“經典”具有普遍性和權威性的本體論意涵。在現代性語境中,“經典化”的開展往往基于美學和史學兩種途徑,“傳統”是文學作品成為經典的歷史前提。在“后現代”的語境中,“去經典化”的傾向會通過揭示經典生成的審美效應和歷史過程,對其背后可能存在的意識形態操作進行批判性審視。這種傾向使得“經典”概念日益失效,因此,有必要再度回到文明傳統脈絡以重啟“經典”的活力。
關鍵詞:經典 經典化 傳統 去經典化 現代性
“經典”在當代已經成為一個泛用的日常名詞,和“高級”“傳統”“品位”等意義群密切相關。我們會在一些商品的分類中看到“經典款”,在電視上看到一些大眾文化作品被冠以“流行經典”的頭銜……諸如此類的表述都拓展了這個名詞的最初意涵。“經典”的本來含義,是指那些為一個民族所普遍承認的、具有權威地位的、內涵豐富的書籍。舉例來說,《荷馬史詩》是古希臘民族的經典,《哈姆雷特》是近代英國人的經典,《詩經》是中國人的經典,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這類經典并不見得從一開始就具備極其崇高的歷史地位。它們也有可能源于大眾文化。在更為寬泛的意義上,說一個大眾文化作品是“經典”,一般是說這種作品流傳時間較久且具有廣泛的傳播度,得到了許多人的喜愛和擁戴,還經得起時間的考驗亦即“耐讀”(無論其是文學作品還是造型藝術、音樂或表演類作品)。因此,大眾文化作品也有成為嚴格意義上的經典的可能。比如,在清代,《紅樓夢》一開始是一部流傳于市井的通俗小說,但隨著歷代讀者、評點家和學者的日益重視,《紅樓夢》也進而被視為嚴格意義上的文學經典。到了今天,關于何為經典的討論仍層出不窮,一些時髦的影視劇或網絡文學,也會由于“粉絲”眾多而獲得“經典”的評價。
圍繞“經典”在當代語境中的“泛化”,一系列理論問題也就隨之出現:人類文明史上出現過的哪些作品足以成為文學經典?文學經典的形成過程是怎樣的?要解答這些問題,我們需要一種歷史的視野,對東西方文明視野中的經典傳統及其建構歷程進行理論化的審視。
一、文學經典的定義與“古今之爭”
要說清楚“文學經典”,我們先得對人類文明歷程中曾經出現過的經典現象進行一番簡單的列舉與歸納,藉此來獲得一些關于文學經典的當代理論所要批判和針對的“正題”。
首先,我們來看看中國傳統中的經典定義。根據《說文解字注》,“經”最初指的是織物的縱向紋理,后引申為天地之間常道常理的文化表征:“織之從絲謂之經;必先有經而后有緯,是故三綱五常六藝謂之天地之常經。”由此可見,“經典”的首要義項之一,是“常”,亦即普遍性。而“典”則是“五帝之書也,從冊在丌上,尊閣之也” ——上古圣王的智慧遺訓所形成的書籍實體,將獲得最高程度的尊崇。由此可見,“經典”的首要義項還包括“尊”,亦即權威性。
普遍性與權威性,或者說中國古代士人所信奉的以“三綱五常”為代表的“萬世不易之法”,由“六藝之學”亦即經學所呈現。對六經亦即《詩經》《尚書》《儀禮》《樂經》《易經》和《春秋》的學習,意味著對普遍高尚的君子品格的學習。正如《文心雕龍?宗經》所概括的:
三極彝訓,其書言經。經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鴻教也。故象天地,效鬼神,參物序,制人紀,洞性靈之奧區,極文章之骨髓者也。
義理與文辭的淵藪,都隱藏在六經及其解釋系統的復雜意義網絡中,等待著有志之士去研習。學習經典,不光是學習文本,還意味著對其著作、匯編和解釋的歷史的學習:“儒家典籍的經典化過程,是一個不斷被稱引和傳述的過程”,“它依賴于不斷地傳承、閱讀、詮釋和信仰”,“具有內在的超越性和原創性,具有打動人的內在魅力”。后來,經學不斷發展,延伸為“十三經”,成為讀書人追求功名、參與科舉的必讀書目。關于“十三經”的各種注疏汗牛充棟,其中也包含著意見歧生的各家各派,如今文經學、古文經學和宋明理學等。直到晚清,經學依然為重大的歷史政治事件提供著理論依據,這方面的代表作當屬康有為的《新學偽經考》和《孔子改制考》。
隨著晚清民國以來現代文史哲的人文學術范式對經史子集四部之學的取代,古代漢語、文獻學、古代史等現代學科開始構成中國古典研究的主要力量。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對過去經典的研究更為規范化、科學化,對中國傳統經典的研究,也獲得了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主義的指導,成為了今天中國經典學的主流方法。正如葉圣陶在為朱自清《經典常談》重印時所作的“序”中所言:“歷史不能割斷,文化遺產跟當今各條戰線上的工作有直接或者間接的牽連,所以誰都一樣,能夠跟經典有所接觸總比完全不接觸好。”作為“文化遺產”,在今天,“經典”中所承載的古老智慧的基本內容并沒有本質性的改變,其中可能傳達的義理,也依然具有生命力。尤其在中華文明的自身確認層面,“經典解釋學”依然具有重要的價值導向。
無論古今,中國的“經典”的定義相對而言比較穩定,其中包含著“普遍性”“權威性”的義項。但“經典”的具體內容和相應的解讀方式,則呈現出“因時而動”“因地制宜”的特征。相比起中國,西方的經典傳統更多體現出民族性、歷史性的特質。這是因為,西方文明的開端是多維的(希臘、希伯來和日耳曼諸現代民族),在漫長的民族交流、沖突和混雜的歷史中,西方不同民族在具體的歷史文化語境中所能夠產生的經驗的深度和廣度不同,他們所尊奉的經典的層次和內涵自然也有所不同。對于法蘭西、德意志、意大利、盎格魯和撒克遜乃至于斯拉夫等民族來說,他們的血緣先祖并非古希臘、古羅馬,他們使用的民族語言并非古希臘語和拉丁語。因此,我們會看到,在漫長的西方現代學術史中,尤其在歷史沖突不斷的時代,好古的古典學立場和反對好古的現代民族立場總是彼此捍格,沖突不斷;在歐洲,“經典”從一開始就作為一個“問題”而存在。
在西方,用于探究各民族之共同經典根柢的學問叫作“古典學”。古典學是“對希臘、羅馬的語言、文學與藝術,以及所有教育我人關乎人之本性與歷史的準確研究”。在文藝復興時期,對古希臘羅馬學問的探究開始盛行,古典學開始登場,并逐漸在近代早期直至啟蒙時代的數百年里,成為人文學問的主要范式,并最終在19世紀成為正式學科。古典學的基本功是古典語文學,即通過對古希臘語、拉丁語和其他古代民族語言的研習,勘察、讀解古代經典文本,結合具體史料,把握文明起源階段的精神樣貌。就其定義而言,古典學毫無疑問旨在為西方文明樹立經典的“普遍性”和“權威性”。自中世紀晚期以來,古典學的興起,使得大量古希臘、古羅馬經典獲得了譯介,西方現代人文主義者在文藝創作方面獲得了可供摹仿的歷史楷模。但丁、彼特拉克、拉伯雷、布魯諾、馬基雅維利和莎士比亞的創作中均體現著古典學的滋養。
但對于現代歐洲民族來說,古代經典雖然提供了豐富的學問基礎,但卻已經無法作為最為權威的知識來源以直面現代生活的種種問題。現代歐洲知識分子大多認為自己站在歷史的進步方向,對現代數理邏輯和博物學知識非常自信,并以此作為依據貶低古代經典在知識上的權威性。與此相應的是一些攜帶著上述現代思想的著作開始被奉為經典,比如馬基雅維利的《君主論》,薄伽丘、拉伯雷與伊拉斯謨的諷刺小說,莎士比亞的戲劇和馬丁?路德翻譯的德語版《圣經》等。“經典”的定義在這一“古今之變”的語境中發生了巨大轉折。與此相伴的,則是近代歐洲爆發的一場曠日持久的“古今之爭”。
“古今之爭”有其具體的政治與社會背景,其核心的爭論焦點,乃是如何看待古代經典和現代經典的品質高低。培根式的“現代派”要擺脫古代經典的權威,藉此樹立起現代經典及其背后的現代性方案的權威。對此,許多堅信傳統經典中富有永恒智慧的“崇古派”提出了反對意見。17世紀英國的“崇古派”代表威廉?坦普爾(William Temple)曾在《論古今學問》(1689)中對當時流行的“崇今派”提出過針鋒相對的批評:
誰要是浸淫于古書,就很難會喜歡上新書……我對知識(knowledge)與學問(learning)作了區分:得到最初發現者或受到教育的后來者首肯,并被公認為真實可靠的東西,我就稱之為知識;學問是指了解前人迥異的、相互沖突的觀點,在這方面,他們或許在任何一點上都沒有達成過一致意見。這樣的區分使古人顯得偉大,現代人顯得渺小。
作為坦普爾的秘書,另一位英國崇古派、諷刺小說大師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則在其接續“古今之爭”的代表作《書籍之戰》(1698)中借古人伊索之口尖刻地指出:
現代派除了熱衷于爭吵和諷刺,我記不得他們還會聲稱有過什么貨真價實的東西……我們古代派……所獲得的其他一切,都出自無盡的辛勞和尋覓,遍及大自然的每個角落。
時至今日,這樣的一些立場顯得“食古不化”,不過其中的確有一點仍值得重視,那就是強調經典應當包含一種普遍為人所承認乃至于尊敬的穩定“知識”;對這種“知識”的獲取不可能一蹴而就,其代價應當是艱辛的學習與鉆研。這也就指出了在現代歷史語境中依然需要悉心研讀傳統經典的本質意義:同時開展認識并完善自身的人格修養訓練,和認識世界、把握至善至美的知識探究。
同時,無論是被動受到自己所生活的時代的生產力和社會具體條件的影響,還是主動關心時勢、直面當下問題,都會讓閱讀者在解讀經典時或多或少附加上歷史性的先入之見。因此,嚴格意義上的對經典的尊奉,或是亦步亦趨地延續古人的教誨,都不大可能在今天成為文學閱讀的主流態度。事實上,在“古今之爭”爆發后的數百年里,為了回應上述問題,關于經典解釋的人文研究獲得了空前的發展,尤其是在20世紀中后期以來,伴隨著批判性意識對經典權威性的“祛魅”,伴隨著形式化的美學方法和社會學化的史學方法的盛行,一種全新的理論視野開始出現,那就是消解本體論意義上的“經典”,對其進行語境式的文本解讀,以求還原這一作品得以“經典化”的整個過程。
二、現代性視野中的文學經典化問題
如果我們承認,文學的核心功能是通過具有審美品味的語言形式,傳達高層次的思想和情感,那么,“經典”毫無疑問就是一切文學作品理應達到的最高境界。當然,如今被視為經典的許多作品在其尚處于大眾文化的階段時,并未嘗顯著體現出對“高層次”的密切期盼。但在廣泛的傳播和被閱讀、解釋的過程中,這些作品逐漸會被“經典化”(Canonization)。
“經典化”的意思是:在專業的批評者和研究者的關注之下,一部文學作品的意義獲得了盡可能多的闡發,其深度和高度得到了明確的驗證,以至于絕大多數人應當可以通過細致的閱讀和解釋,從中獲取智慧與趣味。
這一稍顯冗長的定義,說明了“經典化”這一文學理論現象的復雜程度。一方面,人們意識到,文學作品之為“經典”的本體論判斷,取決于這一作品在歷史中獲得的專業解釋的傳統。沒有對經典的解釋,就沒有經典。另一方面,能夠獲得細致而全面解釋的文學作品,其自身的意義系統必須具備“生產性”。譬如,充滿了隱喻和比擬手法的莎士比亞十四行詩,或者化用典故頻繁、意象連綿豐富的杜甫的《秋興八首》,又或者敘事節奏張弛有度且人物性格紛繁復雜的《水滸傳》,都禁得起來自不同時代、不同層次和不同視角的解讀,給人帶來的感性體驗和思想啟發也連綿不窮。這樣的作品是經典,也是“經典化”的結果。
鑒于“經典化”關涉到作品自身的意義系統,也關涉到作品在歷史接受語境中的解釋學潛能,那么,在當代的文學理論視域里,“經典化”作為一個重要的話題,必然和兩個重要的維度密切相關:一個是涉及文學經典之思想和審美定位的形式論維度,一個是涉及文學經典之歷史性生成的語境論維度。在后文里,我們將會把它們簡稱為經典化的美學維度和經典化的史學維度,并逐一進行介紹。
先說經典化的美學維度。在“古今之爭”的過程中,“崇今派”的基本立場之一,就是以其自身所處的巴洛克時代的審美趣味作為最高且最具典范性的趣味,以此來臧否過往經典文藝作品的審美層次。在“古今之爭”的結尾階段,伴隨著“崇今派”的勝利,西方現代人文經典獲得了學術上的正當身份,過往以傳統經典為范本、認為文藝作品有高低層次的古典主義導向,逐步讓位于一種對“真實”和“日常”頂禮膜拜的現代文學風格。法國批評家圣伯夫(Charles A. Sainte-Beuve)在《何謂經典》(1850)一文中曾提出一種看似“跨越了所有的矛盾與沖突”的現代派的文學經典定義,在后世學人孔帕尼翁(Antoine Compagnon)看來,圣伯夫正是在為新民族國家的民族經典提供正當性辯論。
在此之后,作為哲學分支的“美學”(亦即“感性學”)誕生了,其目的是讓“混亂的認識”和“微小的感覺”可以在歸納中獲得確定性,從而協助現代啟蒙思想,普及現代哲學和人性理念。在這方面,康德可謂居功至偉。在康德《判斷力批判》的巨大影響下,過往關于文學經典的普遍性和權威性的理解,現在逐漸獲得了更為理論化的表述:對于全體人類來說,文學經典的普遍性不在于經典中關于世界和人生的綜合性智慧,而是在于文學作品形式所傳達的美感和由此得來的認識能力的提升:“無須概念而普遍地讓人喜歡的東西,就是美的……美的藝術……的目的是使愉快來伴隨作為認識方式的表象……”同樣地,對于全體人類來說,文學經典的權威性不在于經典的作者在智慧和身份上的卓越,也不在于經典對于民族共同體傳統的偉大影響,而在于作品形式本身震撼人心的意義深度和營造出來的崇高感——后者會在一定程度上激發讀者的內在“敬重”。由此,美感和崇高感取代了一般意義上的普遍性和權威性,成為了現代文學經典旨在追求的美學品質。我們在中國傳統文學批評和現代文學批評的分水嶺——王國維的《人間詞話》——那里,能清晰辨識出康德美學的作用:“無我之境,人惟于靜中得之。有我之境,于由動之靜時得之。故一優美,一宏壯也。”這里的“優美”和“宏壯”,即康德意義上的“美感”和“崇高感”。王國維挪用這對范疇描述中國詩詞經典的兩種最高境界,可以稱得上從現代美學角度對中國傳統文學施行“經典化”的第一人。
如文論家沃爾夫岡?伊瑟爾(Wolfgang Iser)所言:“美學旨在使藝術‘變得有意義’,賦予它以那種只有哲學沉思才可能給出的秩序。”在這個意義上,康德式的美學及其延伸出來的形式主義、心理主義的文論,在現代文學經典化的進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如果沒有18世紀末以來歷代美學家、文藝理論家和文學批評家們對文學本體、文學心理和文學形式的學術探究,經典化的基本原理也就無從說起。在康德的影響下,浪漫主義詩人和理論家如施勒格爾、柯勒律治等率先探究現代意義上的詩學規則,并影響到19世紀的現代主義、唯美主義和20世紀文學批評中的諸多形式主義流派。值得注意的是,作為“形式”而被批評家、理論家們討論的東西,事實上總是與“內容”亦即語言的意向和作者的態度緊密相關,因此,著名文學理論史家韋勒克(René Wellek)指出,這些受到近代美學轉向影響而出場的理論立場,事實上都是浪漫主義有機論的延續,對于他們和后世的學人來說,“……不可能將形式與結構同價值、規范和功能等概念分開;也不可能有一門與美學和批評準則無關的形式與結構或文體的科學”。
如上所述,現代美學理論帶來的“經典化”,實則是通過對過往經典文學文本進行細致入微的形式和意義分析,使之構成現代文學精神的經驗素材和觀念來源的。所以,文學經典化的美學維度中,實則暗含了文學經典化的史學維度。
經典之為經典,在于能夠用非時間性的在場方式,讓其閱讀者再度認識到歷史本身的重大意義。但經典的歷史性生成,則構成了“經典化”的決定因素。在古代,許多被正統精英視為“不入流”的文學形態,后來也因普及度廣、討論者眾而獲得高層文化代言人的青睞,從而被賦予經典身份。具有顯著反叛性的民間小說《水滸傳》,正是因為李贄、金圣嘆等知識分子的評點,獲得了后人的重視。李贄、金圣嘆的這種“命名”和“賦意”行為就體現了“經典化”的歷史功能,通過“與所置身的歷史空間積極對話”,他們使《水滸傳》在明代成為一種代表某種高度與深度的新興的文化形式。
進入近現代,我們可以看到很多經典作品的地位,是由文學史和理論史的書寫所賦予的。比如,在給中國新文學提供歷史正當性論證時,周作人就曾梳理出“載道”和“言志”兩條脈絡,用以概括中國經典文學的歷史線索;與此相伴的,是過往一些不受主流經典統敘所重視的文學現象,如南宋文學、晚明文學、晚清文學等,均被賦予了“言志”的外表,使之與新文學中強調個體自由抒發情感和審美體驗的“人生藝術化”文學風潮發生關聯。周作人的這種歷史書寫,既確認了一些傳統文學經典如晚明小品的歷史地位,也提升了新文學中部分作品的地位,使之成為了“新經典”。
在西方同樣如此。啟蒙時代以來,把經典化的歷史過程還原出來的最具代表性的理論立場,當屬赫爾德(J. G. Herder)以降的近代歷史主義解釋學。赫爾德對《圣經》的人文主義解讀強化了經典的人為詩性特質,借此把《圣經》變成“為人類服務的文本”,從而在宗教地位旁落的時代獲得了文學經典的地位,這也就意味著,民族化的詩人及其對經典的寫作和解釋取代了神圣的宗教之聲,成為了現代世俗化社會的意義提供者。在此之后,諸多浪漫主義批評家紛紛提出從歷史的角度把握過去一些神圣經典的世俗意義的重要性。伴隨著黑格爾《美學》和丹納《藝術哲學》對19世紀的巨大影響,伴隨著馬克思主義在美學和文論領域的普遍盛行,越來越多的文論家自覺從史學、社會學、經濟學、地理學和人類學等領域“取經”,締造各式各樣的經典化解釋。但這些解釋依然有著一種本質主義的動機和目標,即探究經典之本體屬性及其歷史上曾經的對應物的確定的價值品質。比如,赫爾德對近代德意志詩歌的解讀,總是以古希臘羅馬詩人的經典范本作為參照;而丹納即便激烈擁抱一種對美和道德進行調和的黑格爾主義,其中仍透露出保守的特質。因此,不難理解孔帕尼翁為何會轉引伽達默爾的話談到:
19世紀,隨著歷史主義的興起,過去像是超越了時間的“經典”概念開始被用來指一個歷史階段或一種歷史風格……“所有能經得住歷史批判的事物都是經典,因為該事物固有的歷史力量和可保存、可傳承的權威力量將超越所有歷史反思,并在反思中長存。”……既是歷史的,又是超歷史的,歷史的超時性,經典成為一個可接受的關于過去與現在的一切關系的模型。
這樣看來,正如經典化的美學維度中包蘊著經典化的史學維度,經典化的史學維度中也不乏經典化的美學維度的滲透,后者要求史學探究中揭示文學經典之永恒不變的道德和審美價值。甚至連立場相對激進的“新歷史主義”代表海登?懷特(Hayden White),也相信“文學史一定是對恒久性中的變化和變化中的恒久性的表述”。因此,我們不妨認為,對經典化的理論反思,要求對審美形式及其經驗和歷史社會語境兩方面進行深入且綜合性的分析。事實上,大多數學院派研究者已經對這樣的綜合性理論進路達成了基本的共識。
在漫長的描述、分析和批評過程中,綜合了美學維度和史學維度的文學經典研究,最終要呈現出來的就是“傳統”。一個民族的經典作品的序列,往往會構成一種意義明確、內容豐富的“傳統”,并極大地影響著后世文學創作和欣賞者的藝術品味。在著名詩人、批評家艾略特(T. S. Eliot)的理論名篇《傳統與個人才能》(1917)中,“傳統”構成了現代詩人理應作為“知識”去了解的“關于過去的意識”;詩人應當在經典作品所營造的種種感情、感受的經驗的基礎上進行“再創作”,讓這些傳統內容呈現出前所未有的意義。英國著名批評家利維斯(F. R. Leavis)曾把奧斯丁、艾略特、詹姆斯、康拉德和勞倫斯視為現代英語小說“偉大傳統”的代表:這些作家“改變了藝術的潛能”,并且能夠促發“人性意識”亦即“對于生活潛能的意識”;同時,他們都關注“形式”,“把自己的天才用在開發適宜于自己的方法和手段上”,同時又藉此表達“面對生活的虔誠虛懷”和“道德熱誠”;這些作家事實上創造的是“理想的文明感受力”,能夠借助語調的抑揚頓挫和弦外之音的變化促使人類交流,牽動人類的道德體系。由這些例子可以看出,一旦涉及對現代經典的討論,人們必然離不開處理“傳統”。“傳統”是文學作品成為經典的歷史前提,是人們用以投注審美與道德價值以讓“經典化”不斷發生的話語“數據庫”。但“傳統”作為一種預設的穩定價值系統,也就注定會遭遇更為激進的懷疑與批判。
三、后現代語境中的“去經典化”及其反思
自20世紀中后期以來,在激進的后現代文化政治理論的影響下,“經典化”的話題開始逐步轉向“去經典化”(Decanonization)的論域。許多前衛的理論家傾向于通過美學和史學的雙向夾擊,對既定的諸多文學經典展開解構式閱讀,以求拆解“傳統”,挖掘新的美學和史學意義。1971年,美國學者希拉?狄蘭妮(Shelia Delany)為大學一年級學生編選了著名的文集《反傳統》(Counter-Tradition),通過挑選反常規的作品進入大學課堂,來挑戰“官方文化”規定的經典序列;1972年,路易?坎普(Louis Kampf)和保羅?洛特(Paul Lauter)編選了《文學的政治》(Politics of Literature),批判了傳統經典研究中的男性白人中心主義。此后,北美學術界開始了大規模的經典問題討論,其焦點是:那些出自歐洲白人男性作家之手的作品被確立為經典的歷史原因是什么?這背后是否有著意識形態化的操縱?為何不能基于女性主義、后殖民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角度,為普羅大眾樹立截然不同的經典序列?
該如何看待這種由“經典化”問題引申出來的“去經典化”現象呢?如果認為“經典乃是從美學到政治的多重因素合力作用的協商性結果”,那么,基于激進的“文化社會學”,“經典”被“編碼”和“解碼”的過程,就可以得到歷史化的清理,其背后復雜的意識形態與文化領導權問題也就能得到進一步的分析。具體來說,需要得到注意的“編碼”實踐,首先是民族國家和文化的自身塑造,然后是學校、文藝界等公共領域的立法與解釋。而對這些“編碼”的“解碼”,則更多依據后現代理論展開,“把經典看作社會群體意識形態的建構,看作是一種文化政治的表征”,與此相伴的,則是對“審美”的激進解構:“審美的趣味和眼光不過是教育再生產出來的歷史之產物。”而這樣的解構,其實符合大多數當代人的常識。至少,很多人都會提出這樣的困惑:“憑什么我們就該相信,那些被說成是經典的東西就是值得無條件贊美的藝術品?憑什么可以讓我們甘之如飴地放棄自己的審美判斷力而屈從少數幾位權威?”進而,歷史主義的、建構論的經典化理論,會將“什么是經典”的問題置換成“誰的經典”的問題,亦即一個“文化政治問題”。
在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觀點,來自法國社會學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在《藝術的法則:文學場的生成和結構》一書中,布迪厄對過去批評家和作家“殷勤地信奉藝術品的經驗是不可言喻的”的態度感到不滿,認為這是一種非理性的、超驗的狂熱,是一種只注重感覺的“不可知論”;自然地,作為社會學家,布迪厄會聲稱自己的任務恰恰在于把握“在社會世界中產生的”那些“主要的東西”,這種工作更接近反對詩人的柏拉圖式“哲學家”的工作,以“科學分析”來揭示客體和主體的融合,“面對面地觀察事物并依照它們本來的樣子看待它們”。進而,布迪厄提出要關注作為一種社會場域的“文學場”或“藝術場”,把作品視為“被他者糾纏和調控的有意圖的符號”,然后辨認社會場域是如何讓作品的表達沖動變得“難以辨認”的;由此,文學經典的研究,應當更多關注社會空間如何通過“歷史法則的社會煉金術”來抽取“普遍性的升華了的本質”。
布迪厄試圖反對“純”美學的立場。在他看來,“審美”是一種“配置”,是場域的歷史性產物;反之,試圖非歷史地對待作品,借助哲學、法學或神學建構出來的“普遍標準的表象”,極有可能出于“將特殊利益普遍化”的動機。布迪厄這一立場實則為“新文化史”和“新歷史主義”提供了重要的理論支持:“文學表達像科學表達一樣,取決于傳統的規則、在社會意義上建立的前提和歷史地分類構建的模式,如藝術和金錢的對立……”在這種觀點的激勵下,批評家會認為“高雅文化作為統治階級的身份符號,是通過否定‘粗俗大眾’及其文化而確立的”,進而,唯有通過展開對文學經典作品的意識形態化批評,揭示其歷史語境下的話語權力爭奪場景,方能讓我們看到“經典”得以成立的全部生成樣態。
與布迪厄式的立場看似相反,在《西方正典》中,著名文學批評家哈羅德?布魯姆(Harold Bloom)尖銳批評了當代流行的以政治、道德、宗教、種族和其他意識形態為基礎展開文學研究的“憎恨學派”(School of Resentment),堅信應當捍衛文學的“內在性”亦即“審美的力量”。但同時,布魯姆在晚年“致力于對既有的理論進行某種修正和改造”,藉此將“后現代主義的懷疑精神”和文化研究中的“去經典化”結合起來,發展為一種強調“誤讀”的“對抗式”批評。其實,布魯姆的理論態度當中包含著一種將文學批評視為文學再創作的傾向。經典作品在后世作者的焦慮和挑戰中不斷生成為新的作品和意義,而文學批評也是這種生產意義以超越傳統、讓自己擺脫強大前人影響的重要手段。這種“去經典化”事實上包含了對文學史上各種經典得以形成的具體心靈活動的探究性興趣,并同時彰顯著研究者和文學批評者自身的個人詩意沖動和審美快感。可以說,對于布魯姆來說,捍衛經典的原初意圖和歷史地位,這樣的工作遠沒有對經典進行拆解、重構并再度生產各種前所未聞的新穎意義的工作重要。
那么,“去經典化”的理論行動究竟意味著什么呢?其實,“去經典化”的目的,是通過揭示經典生成的審美效應和歷史過程,對其背后可能存在的意識形態操作進行批判性審視,從而挖掘在這些批判性工作的審查后,文學經典還剩余何種確定無疑、具有普遍價值和權威意涵的內容。這樣的批判性工作,恰恰是經典化的美學和史學維度綜合之后產生的題中之義。盡管對傳統和經典的質疑,會引發諸多過激的乃至于過于簡單化的政治指責。
嚴格地說,我們需要一些“去經典化”帶來的精神刺激。在漫長的時間里,經典序列的偉大給知識分子帶來了巨大的壓力,使得對經典的研究成為亦步亦趨的守舊勞作。19世紀末,著名的古典主義者白璧德(Irving Babbitt)曾對現代西方的古典學提出過批評,“追求認識的方法與工具而遺忘認識的目的,這種傾向在古典研究領域中或許表現得最為明顯”。換句話說,在現代體系化、學科化和理論化的知識活動中,經典研讀的意義與價值本身,越來越成為一個艱難的問題。“耐心”而“艱苦”的閱讀,之所以會被流行的理論分析所取代,顯然是后者更有效率,也顯得更具“批判性”,能夠直接作用于對現實世界的理解和改造。在當今國內外大學的文學教育課堂上,經典文本事實上成為了文學理論和批評的演武場。但我們會看到,非凡的理論家大多敬重一般意義上的經典作品,輕慢經典的人其實也并不具備理論思維。優秀的文藝理論與批評家,除了考察他的時代的審美與歷史風氣外,也應當是優秀的傳統經典研讀者。對此,作家卡爾維諾有一個非常精彩的概括:“從閱讀經典中獲取最大益處的人,往往是那種善于交替閱讀經典和大量標準化的當代材料的人。”
而從另一個角度說,經典或許也會因“去經典化”的學術分析配置而獲得新鮮的意義。陳太勝認為:
各種理論在經典文本面前存在著這樣一種吊詭:你覺得自己利用和闡釋了經典文本,并覺得“重新創造”了經典文本,然而,從一個較長的時間看,經典文本毫發未損,受損害的反而是種種處在時間鏈條上的闡釋。
這段話其實辛辣地揭示了諸多“去經典化”的行動最終的歸宿。其實,對于已經為歷史所選擇的經典來說,無論正面的、神話般的解讀,還是負面的、拆解式的解讀,都不可避免要凝視文本自身,以求獲取更多意義潛能。因此,“經典”始終在場,沒有被任何人視若無睹,反而獲得了更多的注意力。“去經典化”因此有可能再度變成“經典化”的一道工序,讓經典文學作品自身的活力一如既往地延續下去。
但這只是一種樂觀的估測。我們會意識到,“去經典化”的趨勢中,如果極端化、簡單化為一種單純武斷的口號,就會帶來嚴重的價值虛無主義。如果僅僅拆解一切通過美學和史學機制“建構”起來的經典形象,而不進行正面的價值引導和闡發,就會讓一些近似于相對主義和政治刻板印象的判斷甚囂塵上。說一切都不是“經典”,恰恰也意味著可以說一切都是“經典”,這也就意味著這個概念在喪失價值判斷的功能。如今,“經典”的標語空前泛濫,但對美和崇高的實在體驗卻越來越弱,相應的生存意義也逐步進入“虧空”狀態。“去經典化”和“再經典化”的話語操作,在這個時代過于頻繁地登場,甚至變成了眼花繚亂的文化經濟,一切“堅固的東西”都在“審美”與“經典”這一組評價性話語的濫用中“煙消云散”。為了捍衛美和崇高等價值旨趣,也就要直面“經典”概念所遭遇的日益顯著的危機。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不得不再度回到文藝自身的審美和歷史機制當中,追問一種關于“經典”的本體論,重啟其應當具有的普遍性和權威性。返回經典傳統,重啟美學和史學的途徑,悉心解讀經典,將串聯起一個文明對自身傳統引以為豪的自覺與自信,有效回應我們時代的意義虧空。
*本文系2021年度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清末民初審美啟蒙論研究”(項目批準號:21CZW009)的階段性成果
作者:馮慶 單位: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

賬號+密碼登錄
手機+密碼登錄
還沒有賬號?
立即注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