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小青、畢飛宇、徐則臣、張清華等名家相聚跨年詩會 文學如燈,照亮我們的“詩與遠方”
當下,文學究竟有怎樣的力量?12月21日晚,在“致敬經典寧聚青春新華之夜”2019-2020南京跨年詩會·“大地的模樣”莫言作品朗讀會上,我們似乎找到了答案。詩會上,張清華、許鈞、何蓮珍、劉偉冬、程永新、范小青、畢飛宇、徐則臣、賈夢瑋、陶澤如、祖峰等多位作家學者、實力演員接力誦讀莫言經典作品片段,文學如燈,照亮前路;詩會外,他們與記者細說文學的今天與未來。

范小青
范小青:每個作家身后都有一片土地
“我和莫言是好友,也是他的仰慕者。”在作家范小青的眼里,莫言有著無與倫比的想象力和充滿詩意、幽默的獨特文字,而這一切離不開其生活的根源和獨特的人生經歷,“每個作家的身后都有一片土地,這給了創作豐厚的滋養,而莫言深扎在他所生活的那片沃土當中,所以才會開出文學的奇葩,再加上他天馬行空的想象力,因此造就了充滿力量的莫言、奇異奇幻的莫言。”
多年來,范小青一直身兼省作協主席和作家雙重身份,但她始終筆耕不輟。怎樣保持充沛的創作熱情?范小青的秘訣是堅持閱讀,“我會集中購買一大堆書,在一個星期里讀完。年紀大了,總擔心自己寫一些令人生厭的陳詞濫調,而閱讀能將我的想象力調動起來,寫作的激情也就很容易迸發出來了。”身為江蘇文壇的女掌門,最令范小青感到驕傲和自豪的是,江蘇文壇一直在蓬勃發展,無論文學隊伍還是文學作品,都位列全國第一方陣,“人員齊整,整體實力強,一代又一代的優秀作家持續不斷地推出好作品。即便在互聯網時代,傳統文學的蛋糕越來越小,但江蘇作家仍然堅守,并且一直勤奮努力,佳作頻出,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情。”

畢飛宇
畢飛宇:讓小切口“抵達”大時代
“我們這一代作家本身就是改革開放的成果。”在作家畢飛宇看來,莫言作品最重要的意義,就是從文學角度對中國改革開放40年的偉大歷程作了回應。“在莫言筆下,人的感觀是如此解放,行為是如此勇敢,每個人都可以做自己身體與靈魂的主人。文學為什么會有這樣的呈現?因為改革開放這一現代化進程中的重大事件重塑了文學和社會的關系,讓作家把筆墨對準人,對準生活,探索中國人在時代變革洪流中如何進行自我認識。”畢飛宇說。
畢飛宇認為,當代文學真正和國家、民族、人民同呼吸,是因為讓小切口“抵達”大時代的文學力量。“人的一生當中有許多‘規定動作’,也有許多‘自主動作’,好的作品永遠充滿了華彩的‘自主動作’,從方方面面讓讀者感知人的生命力,觸摸到現代中國的命運脈搏,體會到作家傾注在筆端的深厚情感。”
“在書香詩韻中迎來新的一年,在我看來特別適合剛剛獲評‘世界文學之都’的南京。”畢飛宇認為,用瑯瑯書聲回望歷史、擁抱時代,賦予了南京這座文學古城更高的檔次、更優質的品位以及更巨大的影響力。

徐則臣
徐則臣:在傳統中尋找新的增長點
“后生切莫欺我老,踏山割云揮破刀。割來千丈七彩綢,裁成萬件狀元袍……”在接受記者采訪時,作家徐則臣吟誦起莫言新作《東瀛長歌》。“我個人非常喜歡它,因為它不僅表達了老驥伏櫪、雄心不改的慷慨之氣,而且體現出這些年莫言一直在倡導的‘向后撤’理念。”
徐則臣舉例說,莫言潛心五年完成的長篇力作《檀香刑》就是一部全面“撤退”的作品:向民間回歸,向說書人回歸,向中國寫作傳統回歸。而《東瀛長歌》跟中國的舊體詩非常接近,“格律長詩這種古典寫作方式,把中國的傳統跟當下生活結合起來,其實是在續接悠久的文學傳統的內容和形式。”徐則臣表示。
莫言的《紅高粱》發表的時候,徐則臣還是個剛上小學的孩子,“可以說我們這代作家都是看著他的作品長大的。我們曾經向他學習充分地敞開自我,學習那種雄渾霸氣的風格,輝煌卓越的想象,我們也將學習他從自身的文學傳統中尋找新的文學生長點的努力。”
文學是曾點燃無數代人的精神火炬,但如今地位有些式微。“通過公共閱讀聚集起作家、藝術家,這是非常有意思的文學創新。”徐則臣說,“不只是詩歌、散文,也應該包含小說、劇本等各種文體。文學不僅僅是文字,它還可以以更多的藝術樣式被人們接受,產生更多的反響。”

張清華
張清華:鄉村敘事也許會換個“方式”
“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后,諾貝爾委員會的頒獎詞指出他創造了一種‘世界性的懷舊’。那是他們的表述方式。用我們自己的話來講,就是莫言寫出了世界性的鄉村社會解體和消亡的過程。”作為多年深耕中國現當代文學領域的專家,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張清華如是說。
在張清華看來,莫言的寫作路徑與20世紀中國文學是一脈相承的。“中國現當代文學的歷史,幾乎就是鄉村敘事或者說鄉土文學的歷史。從魯迅,到許欽文,到趙樹理,他們的作品充滿了高度自覺,具有鮮明的批判性和文化啟蒙色彩,奠定了中國鄉土文學最初的審美基調;而隨著廢名、沈從文的出現,中國鄉土文學又呈現出詩意、溫情和理想主義的一面。莫言筆下對鄉村的贊美與批判,應該說既具有傳承性,又表現了當代作家開拓性的創造和歷史的擔當。”
農業社會的解體是當代中國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今后的中國鄉土文學將會如何發展?張清華認為,莫言式波瀾壯闊、充滿詩意甚至神話意味的鄉村敘事,在當代文學史上留下了深遠的影響。這種影響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很多60后和70后作家作品中都能看到類似的經驗敘述,另一方面,莫言的成功造成了后代作家的“焦慮”,也就是說年輕作者很可能會避開這種地標式的寫作方式,繞道而行走自己的路。“從文學表現來說,全景式、總體性地對鄉村社會進行描摹已經難以為繼了,后代作家的描寫也許會轉變為更具象的、細節化的表達。”張清華表示。

許鈞
許鈞:好的翻譯是一場“歷史的奇遇”
《追憶似水年華》《名士風流》《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曾翻譯過諸多法語文學著作的翻譯家許鈞,將自己的人生之路與中國翻譯事業緊緊結合在了一起。在他看來,不同國家之間的文學語言千差萬別,而翻譯家穿越其間,架起了彼此溝通的橋梁,拉近了世界的距離。
這些年,許鈞除翻譯法國作家的作品外,還一直關注著中國文學在海外的傳播度和影響力。“自從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后,他的作品便越來越受到海外讀者的歡迎,目前已經被翻譯成20多個語種。”許鈞認為,進入新世紀以后,中國文學走向世界的步伐不可阻擋,受到了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越來越多的外國讀者通過中國文學認識了中國人和中國社會,了解了一個時代的精神脈搏,所以說,文學的作用是深刻而全面的,也是不朽的。”
許鈞將翻譯家與作家之間的關系比作成“歷史的奇遇”,一位好的翻譯家,要用自己的慧眼去發現優秀的作家。“如果說一位翻譯家理解喜愛一部作品,他就會把自己融入到作品中,并由此產生一種共鳴。而這種‘共鳴’恰恰是翻譯當中非常重要的部分,因為翻譯家會把作品中深刻的、獨特的精神內涵表達出來。在這一點上,我覺得莫言非常幸運,因為他在英語世界遇到了葛浩文,在法語世界遇到了杜特萊,在瑞典語世界遇到了陳安娜,這些都可謂是歷史的奇遇,這些一流的翻譯家通過差異的語言,把莫言作品真正的靈魂和精神風貌再現了出來。”
幾十年的辛勤耕耘,讓許鈞得到了國內外文學界的充分肯定,在他的推動之下,2008年的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勒·克萊齊奧曾經多次來到中國,與中國作家展開對話。“作為一名翻譯家,最根本的目的是能夠推動這種交流,讓不同文化之間相互學習、文明借鑒,并在相互融合中促進彼此的發展。”許鈞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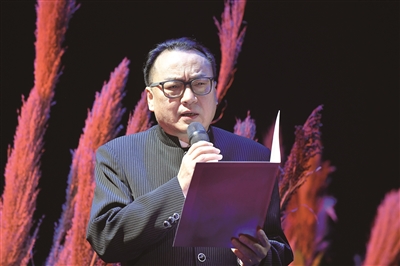
程永新
程永新:文學如水,在生活里慢慢滲透
“好的文學作品,要給讀者傳達出那種離開地面一點的東西。”在《收獲》雜志主編程永新看來,中國當代文學發展三十余年,作家的藝術轉換能力,始終體現在能夠從表面的生存提煉出深刻的問題。“我印象很深的是,莫言作品中總有令人過目難忘的想象,讓讀者感受到那種放大的藝術魅力。比如說他的成名作《透明的紅蘿卜》,‘紅蘿卜’就是一個意象,是一個苦難時期里人對一些美好事物的向往。”程永新說。
回憶起上世紀80年代初初見莫言的情形,程永新如今仍歷歷在目。“那時,莫言在北京解放軍藝術學院上學,我們去找他。他話很少,在交流中以‘李編輯’‘肖編輯’等稱呼我們,讓我們感到驚異,覺得這個年輕人很有才氣,又非常內斂。”程永新說,莫言首次在《收獲》上發表《球狀閃電》就是這一時期,讓他一舉成名的《透明的紅蘿卜》也寫成于這時,“我們看了他的作品后非常喜歡。之后不久他就進入了創作豐盛期,僅《收獲》就發表過他幾十篇作品,一次次帶給我們驚喜。”在程永新看來,從八九十年代的“文學黃金時代”到網絡文學異軍突起的今天,“年輕人的知識結構會有不同,但好的作家仍會以豐沛的創作,以對人性、世界的深刻認識取勝。”
“隨著社會轉型,文學開始降回到它原來的位置。但它仿佛像水一樣,滴落在生活里慢慢滲透。生活、人性、文化、倫理……什么樣的作品才能打動讀者?作為編輯,這其實是對我們的眼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程永新說。

祖峰
祖峰:依托文學,影視劇方能觸動人心
不論是《潛伏》中的特務頭子李涯,還是《北平無戰事》中的崔中石,南京籍演員祖峰扮演的“綠葉”形象總能深入人心。而在現實生活中,祖峰熱愛文學和閱讀,經常與身邊的作家和編劇朋友一起討論“詩和遠方”,稱得上是個標準的文藝男青年。“如果拍戲的話,每天要擠出一個多小時看書,如果沒有拍戲,讀書時間就更多了。”
在熱鬧的娛樂圈,祖峰安靜低調,閑時喜歡閱讀、寫字、篆刻……“練字抄書的過程其實就是讀書的過程,而閱讀對于演員塑造角色而言,是一種無形中的豐富。”祖峰一直認為,影視是離文學最近的藝術,所以演員在表演之余,需要格外增加對文學的親近感,“中國影視與文學之間有著密切的聯系,張藝謀、陳凱歌早期的作品都是改編自中國的優秀小說。”在祖峰看來,影視與文學的終極目的都是要觸及人類的靈魂深處,“一些普通的偶像劇只能說是娛樂產品,只有依托于文學精品的影視劇才更具有抵達人們內心深處的力量。”

賬號+密碼登錄
手機+密碼登錄
還沒有賬號?
立即注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