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藝術就是把實用的變成不實用的——賈平凹、朱中原文學語言對話錄
——賈平凹、朱中原文學語言對話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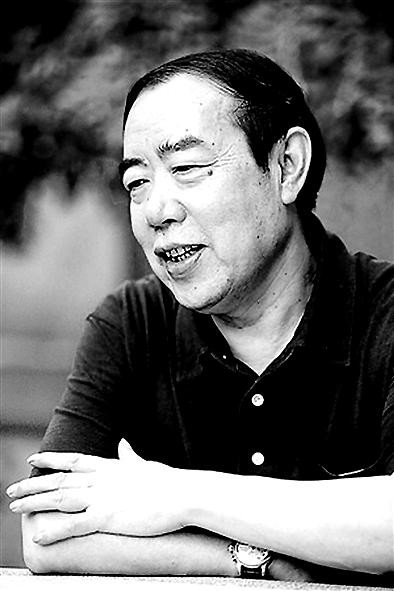
賈平凹

朱中原
如果你沒特點,沒風格,沒有人說你是文體家。一旦形成自己的風格,你所從事的繪畫、書法、文章,都是一樣的。
任何好的作品,肯定都是具有時代特征的,但是不能說具有時代特征的作品就是好作品。好作品與壞作品的劃分標準不是什么時代特征,而是它本身的美感呈現。
“所有藝術的審美都是來源于實用”
朱中原:我覺得現在談文學,不應該局限于一個小范圍,文學應該有大視野,尤其是涉及到語言文體問題,就更是一個大文學的范疇。所以,我覺得非常有必要把文學與書法結合起來談,因為文學與書法都面臨一個漢字與漢語的載體問題。我感覺現在有這樣一個狀況,今天的作家很少關心語言和文體問題,書法家也很少關心書法的語言和氣質問題,這是一種漢語文學與漢字書法的雙重衰退。我曾經提出過一個觀點,叫“筆法退化論”,當然這是針對書法來說的,現在我還要說“語言退化論”,這是針對文學來說的。就是說,隨著時代的推移,書法的筆法和文學的語言,在總體上是一步步退化的,這種退化無可阻擋。
賈平凹:漢語和書法的衰退主要是書寫工具造成的。上世紀30年代的作家大都用毛筆,當然他對書法的體悟肯定就比較直觀和真切,現在的作家不要說不用毛筆,甚至發展到連鋼筆也不用了,直接用電腦,也許再過很多年,人也不用腦子思考了,直接在電腦上敲。從這個角度來理解書法與文字語言的關系,其實研究每一個語言和漢字,都可以體會漢語文學的奧妙。漢語有一個結構美。什么樣的語言是好語言呢?我理解,能準確表達出此時此地的情緒的語言就是好語言。要表達情緒,一個主要的手段就是節奏問題,語言、語句好不好,主要是節奏問題。語言和身體有直接關系,語言為什么要用逗號、句號、問號、嘆號等等之類,它是與人的呼吸有直接關系的,你的呼吸系統有多長,語言就有多長,呼吸有多短,語言就有多短。有人故意追求短句或長句,首先就不符合人體結構。
朱中原:從某種程度來說,語言是人的氣質的反應,更直接地說,語言是人的身體系統尤其是生理系統的反應。
賈平凹:所以,書法里的結構,咱先不說它是一篇文章下來,就是單個字里也有它的節奏,把一個字一個字連起來形成一幅作品,它里面更需要節奏,它的快慢緩急,和文字語言的要求是一樣的。審美都是相通的。會寫字的人,知道把那種文字變成這種文字,那寫出來的就是漂亮文字。另外,什么叫藝術?我覺得把實用的東西變成無用的東西,就是藝術。比如書法,最早是實用的,其實很多時候都是實用的,是用于記錄的載體,后來慢慢慢慢失去了實用性,追求審美,就變成藝術了。繪畫也是這樣,最早是給人畫個肖像,用于記錄,慢慢就變成另一種審美了。
朱中原:所有藝術的審美都是來源于實用。
賈平凹:是的,比如勞動時,吭哧吭哧的,這是一種實用,但發展發展,就出現了模擬這種音的詞語,再發展,就形成了歌曲。
朱中原:文學語言是一種藝術化的語言,但它是對于現實生活、自然社會和實際事物的一種描摹,就像你作品中的很多語言,大多來源于地域方言的文學化的改造。
賈平凹:這與寫《文學概論》的那些語言專家說起的語言是兩回事。只有能準確表達情緒的語言,才是好語言。長句子短句子,急促緩慢等等,各不相同。最早我研究語言,我就把很多特別好的歌曲反復聽,我也不會唱歌,但是我能聽,哪首歌特別好聽,為啥好聽,我還是清楚的,我是拿工業圖紙,在小格子上標上哆來咪發梭拉西哆,雖然我不認識簡譜,但能看出音節的高低起伏,緩急節奏,你就會發現,高了以后很快就低下來,低了以后就很緩慢,一般都是特別急促的旋律之后好長一段時間才逐漸舒緩,從中可以看出節奏變化,寫文章的時候,就自然而然地具有這種節奏,可以把文學語言搭配得更生活化、口語化和富于節奏變化。
朱中原:我的體會也是這樣,我有時候聽歌,尤其是聽長江三峽一帶的民歌的時候,或者去實地旅行考察的時候,突然就會有靈感,然后寫上幾句,我并沒有刻意模仿誰的句子,但有人說,你的詩有《竹枝詞》的風格。起初我沒太注意這個,但后來發現,還真是有點。后來我就在想,為什么一個不會寫詩的人,寫出來的詩卻帶點《竹枝詞》的味道呢?原來是我們受了共同的影響,那就是巴楚民歌的元素。劉禹錫正是因為受了巴楚民歌的影響,才有了《竹枝詞》,所以詩句特別清新明快,旋律很清脆,就是有歌的影響。
“高明的小說家都善于寫閑話”
賈平凹:你前不久發給我的詩就有點這個味道,里面還有漢樂府的意味,不通音律的人是寫不出這個感覺來的。另外我還有一個文學創作奧秘,寫小說就是要多說閑話,閑話也就是廢話。你不說這句話,這個句子也明白,但是把正經句子說完,后面再說一兩句別的修飾話或加強語氣的話,句子一下子就有味道了。
朱中原:高明的小說家都善于寫閑話。其實我看你后期的小說,已經不再是宏大敘事,沒有特別強的故事情節的起伏跌宕,沒有特別明顯的矛盾沖突,小說中的幾乎每一句話,說的事情似乎都是可有可無的,實際上就是一些日常生活瑣事,或者叫家常話、家常事,我覺得你尤其擅長的是女人與女人之間的繁瑣對話。我覺得你現在的文學手法,已經趨于這樣的穩定化,讀來有一種蒼蒼茫茫、混混沌沌之感,于平淡中見天真。
賈平凹:這個也是靠自己慢慢積累、慢慢體會得來的,別人跟你說的創作手法不一定適合你,因為各人情況不一樣。
朱中原:其實古今中外,幾乎所有的文學經典,都善于寫閑話,《紅樓夢》善于寫閑話,《金瓶梅》善于寫閑話,張愛玲善于寫閑話,魯迅善于寫閑話,林語堂善于寫閑話,沈從文善于寫閑話,汪曾祺善于寫閑話,《百年孤獨》善于寫閑話,反倒是那些通俗文學,基本不寫閑話,只講故事情節,但是這些東西離嚴肅文學恰恰很遠。正因為這樣,我覺得一個高明的作家,才善于從瑣碎的日常生活中觀察和模擬語言,并從中體味到語言的味道和魅力,進而創造文學語言。其實語言也是需要創造的,但這種創造來自生活。生活是一切創造的源泉。不管學啥,書法、繪畫、音樂、舞蹈還是文學創作,功夫都不在本身,而恰恰在身外,不一定天天都要創作。我平時有一個習慣,到哪一個地方,就喜歡琢磨那個地方的語言,聽他們的語言與普通話之間的差距,與過去古語的聯結點。我就發現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恰恰是很多偏遠地區,保留了比較多的古語的習慣,比如青海,雖然地處青藏高原,但它的方言里恰恰有很多古語的成分,我舉一個例子,有一首“青海花兒”叫《面匠哥》,歌詞里有這么一句:“昨晚夕睡夢里把你夢見了。”哎呀,我一聽歌詞好美,美在哪里?“昨晚夕”,“昨晚夕”就是昨晚上的意思,青海人說“晚上”說“晚夕”,“晚夕”就是古語,說“夢見你”叫“把你夢見了”,這是把字句。把字句突出了被夢見的主體,這比起說“夢見你了”更有意味,情感色彩更濃。后來我在思考,為什么青海這么偏遠的地方卻有那么多古語色彩,原來現在大部分青海漢族都是明朝時候從南京的烏衣巷遷過去的,明朝形成了一個大規模的人口遷徙潮,人口遷徙的同時,自然也把內地的語言習俗帶過去了,而南京話恰恰就是過去的中原官話,因為南京是六朝古都,六朝時期的南京人,大部分也是從中原地區遷徙過去的,所以南京話恰恰保留了中原官話比較多的元素。
賈平凹:原來你對語言還有這么深的研究和體會,這種功夫,恐怕是那些天天趴在那寫字畫畫的人弄不出來的。我的感覺是,你如果天天趴在那寫字,那自然不行,把人寫疲了,審美也會出現疲勞,但如果中間干點別的啥事來體會一下,反而會更有效果,就是從別的方面體會藝術的魅力。如果一個畫家,每天上班就坐在畫室畫畫,你天天都在畫,你能畫個啥嘛,你天天畫就畫疲了嘛,沒啥可畫了嘛。
“文體說到底也是語言風格問題”
朱中原:繪畫語言跟文學語言、書法語言本身是相通的,只是表現手法不同而已。你把觀察到的東西,用畫面和色彩表現出來,然后進行語言的提煉,或者是把文學的文字,變成畫面,這就是美的繪畫語言。美的繪畫語言,其實就是詩,就是文學,畫面上的筆墨線條和空間組合,也是可以形成節奏感的,這種節奏感,和文學中的節奏感差不多。只不過文學的節奏感,是通過文字來體現,繪畫的節奏感,是通過筆墨和色塊來體現。說到這我想起你的繪畫,我覺得你的繪畫語言非常豐富,就來自你的文學語言,你的文學語言也多借鑒于你的繪畫語言。我發現,把你的繪畫作品一張一張擺在一起,連起來,然后用最樸實的語言一點一點描述出來,就是一篇很好的美文。好的文學語言,它就是畫么;好的繪畫語言,它就是文學么。這就是一個在文學語言和文體上有深厚造詣的文學家的繪畫與一般職業畫家的不同之處。我認為,一個優秀的文學家,首先應該是一個優秀的文體家,至少也應該是一個在文體上有深厚造詣的人。
賈平凹:文體說到底也是語言風格問題,語言風格問題說到底也是文體的問題,每個人跟每個人不一樣么。就像做菜,我要做川菜,就是特別辣,我要做粵菜,就是要會做海鮮,我要做淮揚菜、東北菜,或是陜西菜,不管咋,你一定要有你自己的特點。對于美食家來說,除了辣之外,恐怕還要做到鮮美,它需要講究味覺、視覺、觸覺等等,這都是需要慢慢積累、慢慢體味的,而且要有自己的追求和審美修養,這才能形成自己獨特的風格。文體也是這樣,你首先得尋找你自己和別人不一樣的、你自己感興趣的句子風格,這一句話,你要那樣說,我偏不那樣說,只要你把話說好了,自然會形成你獨特的句子風格,慢慢地你有了自己的特點,你就和別人不一樣了么。如果你沒特點,沒風格,沒有人說你是文體家。

賬號+密碼登錄
手機+密碼登錄
還沒有賬號?
立即注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