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的文學經驗、文化實踐與社會構造
2017年11月18日,“新中國視域中的文學經驗、文化實踐與社會構造——首屆人文社會跨學科青年學者工作坊”在廣州召開。此次會議由中山大學青年學者羅成擔任召集人,中山大學中文系主辦,邀請了來自文學、史學、哲學、社會學等領域十余位學者,圍繞新中國的文學、文化、社會等相關歷史經驗與歷史實踐問題共同參與討論。

活動現場
中山大學教授張均首先指出,十七年文學(編者注:十七年文學至自1949年建國至1966年文革開始之前的這一階段文學歷程)一直是現當代文學領域關注的重點。過去對十七年文學的研究多局限于文本內部闡釋,因此,有意識地運用田野調查方法,把文學經驗、文化構造和更大的社會實踐聯系起來,對于今后的研究來說應是一種有益的探索。《開放時代》特約主編、中山大學哲學系教授吳重慶認為,要高質量地研究新中國以來的“兩個三十年”,須將眼光放得更長遠,關注1919-1949這一建國前的三十年,才能幫助我們更精準地把握1949年以后的國家建構問題。在此基礎上,他提出兩個議題:第一,新中國“新”在哪里?他主張用“革命視野下的革命史研究”來突破現有研究對于國家與社會關系的二元對立認知,重構對建國初期政治實踐與人心狀態的理解;第二,新的中國研究“新”在哪里?他認為,十七年文學是真正底層的發聲,對十七年文學的同情之研究,能夠成為真正突破既往研究以精英為關注重點和素材來源的可能性。他敬佩以柳青為代表的一代作家,敬重他們對整個時代、鄉村、人群全方位、全身心的投入和認知。此間歷史與經驗的豐富性,有待于包括此次活動參加學者在內的眾多有心人去重新發掘和利用。
羅成隨后指出,中文學科的意義不僅是研究傳統文化,更需要關注當代問題,具備當代意識,這也是他召集此工作坊的緣起和主旨。要悉心體察與了解新時代的歷史脈絡、現實經驗與未來走向,就應在研究中堅持以“問題”而非“學科”為中心,從跨學科視域出發,充分發掘與闡釋新中國的自我理解、社會理解與國家理解。欲恰切理解“新時代”,就先須恰切理解“新中國”,新時代和新中國的“新”,就根本而言是繼往開來的“日新之謂盛德”意涵,也是“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這一傳統精神的現實彰顯,這其中蘊藏的正是中國、中國人與中國社會關于日新月異之感的特殊自我理解。當代中國的學術思想,需要從自我認識、自我期待與自我創造的豐富理解出發,去體貼地把握新中國與新時代。
“順”與“安”:新中國的人心感覺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何浩在其題為《<創業史>與建國初期的創業史——再造“中國”的歷史經驗與思想意涵》的演講中指出,這一報告屬于“社會史視野下的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整體研究計劃的一部分。該計劃有別于既往將文學與政治相對立的認知框架,重在強調新中國政治對于社會基體加以改造和翻轉過程中呈現出的新狀況,而很多文學家正是在投入這一改造和翻轉活動的過程中,發現了新的經驗和創作敏感點。該計劃旨在將既有的歷史敘述空間進一步撐開并加以討論,從文學的視角來重新看待政治對于社會基體的改造作用。何浩進一步指出,柳青寫作《創業史》的過程,實則非常深地扎根于中共改造社會基體的政治實踐,由此,柳青敏銳地觸碰到了政治打造社會的實踐過程中最核心、也是最困難的地方,并對此給出了自己特殊的思考。這些思考無法被簡單回收到關于新中國初期合作化運動的既有敘述中,如國家工業化與農業合作化的關系這一討論框架。柳青思考的特殊性體現在他筆下呈現的新的中國社會及其人民的“性氣”問題。基于自身的人文意識,他察覺到了“性氣”這一影響社會發展的重要層面,而這一點在后來的歷史敘述中均未被關注與討論。就此,何浩給出了自己的理解:討論新中國之所以“新”,即是要討論該時期中國如何捋順中國人的性氣,如何使之有新的發舒。以此意識為認知前提,我們對經濟機制和社會組織方式的考慮才會更加長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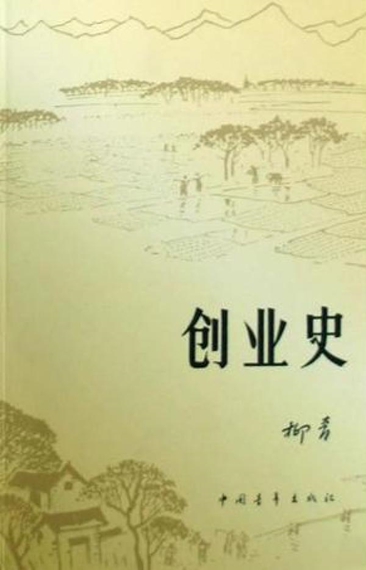
柳青《創業史》
同樣是在社會史和精神史的視野下討論新中國語境中人的身心感受,羅成作了題為《安心的戰爭——作為建國史詩的<銅墻鐵壁>》的報告。他表示,《銅墻鐵壁》這一長篇小說的創作過程處于1949年建國前后,由此,他想通過細致的作品分析,厘清此小說內在包含的藝術感覺與建國初的歷史整體感覺所具有的緊密關系。他從對于“史詩”這一文學批評概念的理解入手,指出了這篇小說對新人形象、新社會狀態理解的重要性與特殊性。既有對該小說的分析中,石得富、普通老百姓、石永公分別被歸納為先進、普通、落后這三種類型,而由上述批評視野所提供出來的認知思路與感覺結構出發,重新考察小說中的這些人物,羅成發現,既有分析仍存在推進的空間。可以說,柳青對于這些人物形象的塑造并非本質化的,而是歷史的。因此,在柳青的理解中,通過戰爭實踐的有效打造,普通群眾在流動的心緒變替、行為轉化過程中真正實現了自我的認識與改變,這才是對中國革命得以勝利的、深入歷史人心的恰切理解。羅成總結道,柳青把握并最終寫出了戰爭賦予人民的安心品質,其中包蘊著柳青對“人民戰爭”和“人民中國”的獨到理解。
下鄉·家庭·工廠:新人的歷史感覺
在新中國的身心感覺下,歷史中的人如何生成更好的狀態?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程凱圍繞他的論文《理想人物的表現方式與認識意義——“梁生寶”人物形象的再審視》展開了自己的思考。他認為,“參不參與革命”與“有沒有馬克思主義理論”這兩點并不構成“社會主義文藝”與“五四文藝”之間兩種文藝家的本質區別。重新認識中國社會的動力和能量從哪里來,這才是理解社會主義文藝的出發點。程凱尤其強調,欲理解40年代后從根據地成長起來的這批作家的文學感,就特別要注意其政治感的調整。他指出,共產黨的政治要求和社會重構的現實共同促成了作家政治感和現實感的變化,進而激發了他們以新形式把握中國社會的愿望和能力的形成。整風運動突破了新文化運動之后形成的思想慣性,因而可被視為對當年的啟蒙者構成的反向啟蒙。程凱以柳青整風運動后的“下鄉”經驗為例,說明了柳青對自身的再造恰恰是內化整風的歷史要求和藝術要求的結果。
中山大學中文系郭冰茹關注女性主體的成長,做了題為《“新人”的長成:一個性別的視角》的報告。她指出,思考“新人”的核心概念是公私對立。在新人長成的過程中,由于女性還需要特別面對家庭問題,因而常常處在“私”的空間中。由此郭冰茹發現,十七年文學作品的主人公如果是女性,那么她所需要面臨的問題就會比男性更復雜,相應地,其自我改造的可能也會更徹底。女性的性別認同、個人認同始終與“現代民族國家”這一宏大敘事糾結纏繞在一起。歷史地看,在五四時代,當女性走出家庭、步入社會,時常就會面臨自我認同與性別認同的調適難題、以及如何平衡家庭與社會關系等問題。而在十七年文學的短篇小說中,我們卻能夠看到,性別認同得以擺脫五四以來通過情感、婚姻、職業生活等中介建立起來的性別認同體系,最終能夠將自我認同和新人成長結合起來。這一批作家共同特點在于,他們把家庭幸福和投身社會主義建設放在一起看待。
著眼于時代轉向中的新人,首都師范大學文化研究院符鵬作了題為《再造社會主義新人的內在危機及其歷史內涵——以蔣子龍的小說<赤橙黃綠青藍紫>為中心》的報告。他力圖以對這篇小說的理解為契機,觀照新時期中國社會中若干新的歷史展開及其意涵,并進一步考察前三十年社會主義經驗在新時期這個歷史階段如何被重構。他認為,作家蔣子龍在文學創作領域的出現與五十年代天津工廠的生產和文化機制緊密相關。蔣子龍在1958年進入工廠并加入文宣隊,通過與工廠不同層面的互動,他逐漸接觸并對工廠各層次問題形成自己的理解方式。由此符鵬點明,蔣子龍所倚賴的思想教育路徑和管理方式的再調整,這種對問題的處理方法是由六十年代經驗構造出來的,而這其中保留了可貴的經驗。因此,作為后來人的我們需要深入分析社會主義中國所構造、形塑的文學、社會、政治理解到底是什么,這些理解如何供以蔣子龍機會,使其得以在歷史的轉折過程中進行高度的自我磨練,進而對現實有所把握和調整。反過來看,這些歷史視野及經驗中未能被充分消化的部分,也最終成為了蔣子龍此后創作有所局限的根源。

“真”與“誠”:新視野的思想感覺
張均作了題為《重估社會主義文學遺產》的報告。他表示,他所理解的社會主義文學主要是指1942-1976年間的文學,它有以下三個貢獻:第一,社會主義文學大量再現了中國下層人的人生遭際,尤其揭示了民國時期普通人在土地權利和經濟壓制下的生活。在用成長模式寫正面人物和用喜劇方式寫反面人物方面,社會主義文學也有自己的特色。第二,發現社會。社會主義文學真實地看到并聚焦于鄉村這一中國最廣大社會的集中點。但是,只容許階級作為主要線索,這與由階級、宗族、鄉土、宗教多元構成的真實社會仍有距離。第三,新文化創造。毛澤東時代對文化的創造是將下層的人視為文化認同的中心,這種文化呈現出平等、勞動、集體主義三個特征。張均的總結是,社會主義文學作為中國文學史上的特殊類型,兼有“債務”和“遺產”的意義,長遠來看,其正面意義將會得到更多肯定。
從現代性視野出發審視歷史,中山大學博雅學院肖文明作了題為《文藝與政治:現代性視野下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再思考》的報告。他認為,毛澤東對文藝和政治的看法反映了中共對中國現代性的塑造努力。借用鄒讜的觀點,肖文明意在說明,晚清的滅亡是政治文化高度一體化體系的崩潰,而中共對這一危機的回應,是通過革命重建一體化秩序,雖然如此,我們仍要看到,在現代性背景下,這一體系依舊要容納分化的成分。這種新的多元現代性與傳統一體化之間存在的張力,至今是我們要面對的挑戰。他進一步指出,毛澤東思想的一元化傾向與傳統有關,也就是對人和人心重要性的關注,這體現于他對思想和文化觀念的強調。借助帕森斯關于價值和規范的討論所開掘的視野,肖文明討論了文藝服務于政治的內涵,一方面強調了對價值共識的普遍約束性,但同時仍具有尊重文藝這一專門領域自身的邏輯,而這是強調政治和藝術相統一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所在。他指出,由于革命動因埋藏在更深遠的歷史當中,因此深入理解傳統和革命之間的辯證關系,不僅是當代中國人理解過去的必需,也是展望未來的前提。
重慶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金浪作了題為《朱光潛的土改觀察與思想改造》的演講,試圖將“土改”作為把握朱光潛思想轉變的一個環節。他指出,朱光潛在1949年的檢討僅僅批判了自己跟現實的脫節,盡管他在表面上逐漸學習和接受馬列主義,但其具體的美學認識和唯物主義認識之間仍有較大距離。1951年,朱光潛在參與土改實踐后寫了《從參觀西北土地改革認識新中國的偉大》一文,從治人和治法的獨特理路解釋民主專政、群眾路線、統一戰線這些問題,這與之前的認識形成了鮮明對比。金浪從此思考中發現,朱光潛對自己認知階級問題的方式進行了清晰描述。中共帶動鄉村人民獲得教育、使其主體性得到發展,由此他們獲得了更飽滿的狀態,朱光潛正是從中共的這一工作方法中受到觸動,他自己的情感也因此發生了巨大變化。金浪認為,朱光潛有意識地把土改中群眾和工作組的批評與自我批評這一工作方法、以及此過程中帶出的現實感納入到自己的檢討中,上述變化是他不斷反思和改造自身的結果。

賬號+密碼登錄
手機+密碼登錄
還沒有賬號?
立即注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