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淵沖:“讓中國的美成為世界的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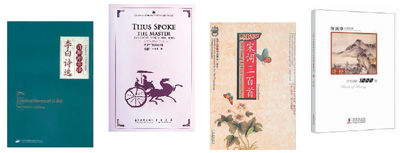
許淵沖部分譯作
怎么也沒想到一代宗師住得如此“寒酸”!2017年秋,北京大學(xué)暢春園,走進(jìn)96歲的翻譯家許淵沖先生簡陋的住處,筆者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水泥地面,到處堆的是東西,斑駁的墻壁,泛出“歷史感”。逼仄的門廳迎來幾個(gè)外人,頓時(shí)無法立足,只能趕緊把自己塞進(jìn)小床對面的沙發(fā)上。
北大30多年,就是在這間陋室,許先生翻譯了上百本中英文經(jīng)典,成為“詩譯英法第一人”,2010年獲得“中國翻譯文化終身成就獎(jiǎng)”,2014年摘取翻譯界最高獎(jiǎng)項(xiàng)——國際譯聯(lián)“北極光”杰出文化翻譯獎(jiǎng)。120部中英法文譯著,碼成我們身后書架上浩浩蕩蕩的學(xué)術(shù)疆域。
“貝多芬說得好,為了更美,沒有什么清規(guī)戒律是不能打破的”
“我這一生,先是不斷超越自我,學(xué)習(xí)別人,提高自己,最后做到超越前人,攀登高峰。”
許淵沖早年畢業(yè)于西南聯(lián)大外文系,1944年考入清華大學(xué)研究院外國文學(xué)研究所,1983年起任北京大學(xué)教授,被稱為國內(nèi)能夠?qū)⒅袊诺湓娫~譯成英、法韻文的唯一專家,前后翻譯了《詩經(jīng)》《楚辭》《李白詩選》《西廂記》《紅與黑》《包法利夫人》《追憶似水年華》等中外名著。
“20世紀(jì)英國詩人艾略特說過,一個(gè)藝術(shù)家的發(fā)展過程就是不斷地為了更高的價(jià)值而做出自我犧牲。中國物理學(xué)家李政道也說過,發(fā)現(xiàn)前人的弱點(diǎn)并超過他們,就是突破”。許先生風(fēng)趣地將70多年學(xué)術(shù)歲月,按照但丁《神曲》的分法,分為“青春”(1921—1950)“煉獄”(1951—1980)和“新生”(1980——)三部曲。即“五十年代教英法,八十年代譯唐宋,九十年代傳風(fēng)騷,二十一世紀(jì)攀頂峰”。他解釋說,上世紀(jì)50年代以前,基本是學(xué)習(xí)繼承時(shí)期,同時(shí)注意前人的弱點(diǎn),準(zhǔn)備超越。上世紀(jì)80年代以前是改造時(shí)期,浪費(fèi)了生命中的黃金時(shí)代。1980年以后才開始了超越時(shí)期,成了“書銷中外六十本,詩譯英法唯一人。”
超越意味著創(chuàng)新。在學(xué)術(shù)界,許淵沖被稱為“在翻譯上打破了很多框框”,也因此產(chǎn)生了一些爭議,比如,認(rèn)為他的翻譯與原詩差別較大,意譯的成分較多。但許淵沖至今堅(jiān)持自己的理念,“按照他們的觀點(diǎn),忠實(shí)原文逐字翻譯最好,翻不好也沒關(guān)系。但我認(rèn)為,翻譯的忠實(shí)不僅要忠實(shí)于形式,更要忠實(shí)于內(nèi)容。內(nèi)容形式統(tǒng)一時(shí),我不離開形式;內(nèi)容形式矛盾時(shí),我選擇內(nèi)容。如果我的表達(dá)形式比逐字翻譯的形式更能傳達(dá)原文的內(nèi)容,那我會(huì)選擇我的表達(dá)方式。”
許淵沖的翻譯理念,也是逐步形成的。上世紀(jì)30年代,翻譯作品流行全國,魯迅的直譯很為進(jìn)步作家所接受,許淵沖也不例外。但當(dāng)時(shí)的他更喜歡朱生豪翻譯的《莎士比亞》喜劇,傅雷翻譯的巴爾扎克和羅曼羅蘭的小說,比如朱譯的羅密歐和朱麗葉,最后兩句“古往今來多少離合悲歡,誰曾見這樣的哀怨辛酸?”幾乎可以說是勝過了原文(原文直譯:世界上的戀情沒有比得上羅密歐與朱麗葉的)。從前人的實(shí)踐來看,許淵沖認(rèn)為直譯不如意譯。
西南聯(lián)大時(shí)期,錢鐘書提出翻譯的“化境”,對許淵沖產(chǎn)生了很大影響。他在《林抒的翻譯》一文中說,“譯者運(yùn)用‘歸宿語言’超過作者運(yùn)用‘出發(fā)語言’的本領(lǐng),或譯本在文筆上優(yōu)于原作,都有可能性。”許淵沖認(rèn)為,這并不是說譯者文筆優(yōu)于作者,而是說“歸宿語言”(譯語)的歷史比“出發(fā)語言”(源語)更悠久,內(nèi)容更豐富,具有一種優(yōu)勢,而譯者充分發(fā)揮了這種優(yōu)勢,使譯文勝過原文。錢先生在給許淵沖的英文信中說,“你當(dāng)然知道羅伯特·弗洛伊德不容分說地給詩下的定義:詩是‘在翻譯中失掉的東西’,我倒傾向于他的看法,無色玻璃的翻譯會(huì)得罪詩,有色玻璃的翻譯又會(huì)得罪譯”。
在許淵沖看來,無色玻璃的翻譯重在求真,有色玻璃的翻譯重在求美,但是翻譯不可能做到百分之百的真。他反問,文學(xué)創(chuàng)作是創(chuàng)造美的東西,而文學(xué)翻譯則是為全世界創(chuàng)造美。就翻譯而言,求真是低標(biāo)準(zhǔn),求美是高標(biāo)準(zhǔn)。譯文如果只求其真而不求其美,能算忠于原文嗎?
作為第一個(gè)獲得“北極光”獎(jiǎng)的亞洲人,老先生把這個(gè)獎(jiǎng)看作是對中國文化的肯定,也是對他的翻譯方法的肯定。他認(rèn)為,與西方語言內(nèi)容等于形式不同,中文其實(shí)是內(nèi)容大于形式的。包括英文、法文、德文、西班牙文在內(nèi)的西方文字之間有90%可以對等,彼此翻譯很容易。但中文不同,中文與英文的對等率不到50%,也就是說不對等的大部分就需要翻譯來做工作。中英翻譯比英法翻譯難一倍以上。這就是為什么國際翻譯界,英國人法國人拿一個(gè)大獎(jiǎng),不是什么難事,但亞洲人很難。
“貝多芬說得好,為了更美,沒有什么清規(guī)戒律是不能打破的”,許淵沖堅(jiān)持翻譯不應(yīng)持“對等論”,而應(yīng)取“優(yōu)勢論”,翻譯時(shí)“要多從中國文化的內(nèi)涵和優(yōu)勢上想”。按照這一理念,許淵沖形成了自己中國學(xué)派的翻譯學(xué)說:“音美、行美、意美”三美,“形似、意似、神似”三似,“知之、好之、樂之”三之。
“要是李白活到當(dāng)世,也懂英文,必和許淵沖是知己”
在許淵沖看來,通過翻譯的文化經(jīng)典,不僅要讓讀者“知之”,懂得其真,且要“好之”,發(fā)現(xiàn)其善,最好是“樂之”,感受其美。如果把“千山鳥飛絕”翻譯成“一千座山”,把“人閑桂花落”翻譯成“懶懶的人”,如何能體現(xiàn)天地之間纖塵不染的那種孤獨(dú)寂靜以及花開花落聽之任之的那份閑情逸致?
中國詩詞往往意在言外,英詩卻是言盡意窮。中詩意大于言,英詩意等于言。如果言是一加一,意是二,那英詩就是1+1=2;而中詩是1+1=3。李商隱“春蠶到死絲方盡”,如果只表示春蠶到死才不吐絲,那就是1+1=2;如還表示相思到死才罷休,那就是1+1=3;如還表示寫詩要寫到死,那就是1+1=4了。更別說“絲”與“思”通這種奇妙,又該如何向西方人傳遞?
讓許淵沖頗為自豪的是,他的譯文國外很認(rèn)可。英譯《楚辭》被美國學(xué)者譽(yù)為“英美文學(xué)領(lǐng)域的一座高峰”,英譯《西廂記》被英國智慧女神出版社評價(jià)為可以和莎士比亞的《羅密歐與朱麗葉》媲美,他確實(shí)做到了“讓中國的美成為世界的美”。
比如,唐代李白的《靜夜思》,中國人看到又圓又明的月亮,就能想到故鄉(xiāng)。外國人沒有這種文化背景,他怎么可能明白呢?若是按字翻譯成:向上望看到月亮,低下頭想到故鄉(xiāng),外國人肯定想中國人寫的這到底是啥玩意,這都能叫做詩?“我翻譯時(shí),把月光比作水,英文譯成‘月光明亮如水,溺住了那些思鄉(xiāng)的人。’用水把月亮和鄉(xiāng)愁聯(lián)系起來,文字上又有英語的優(yōu)美,他們就理解了。”1987年,許淵沖英譯《李白詩選一百首》出版,錢鐘書的評價(jià)是,要是李白活到當(dāng)世,也懂英文,必和許淵沖是知己。
葉公超在他的《散文集》中引用了艾略特的話:“一個(gè)人寫詩,一定要表現(xiàn)文化的素質(zhì),如果只表現(xiàn)個(gè)人才氣,結(jié)果一定很有限。”其實(shí)翻譯也一樣,最終體現(xiàn)的是文化素質(zhì)。中國古詩意蘊(yùn)復(fù)雜,一首詩幾乎都有多重意思。比如《詩經(jīng)·采薇》中的名句“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一向被認(rèn)為是《詩經(jīng)》中最美的詩句,如何翻譯才能傳遞這種美?
王國維在《人間詞話》里說過,一切景語都是情語。“依依”不但是寫楊柳飄揚(yáng)之景,更是寫依依不舍的征人之情。“霏霏”不但是寫雪花飛舞之景,更是寫征人饑寒交迫之情。如果就按照字面翻譯,達(dá)意而不傳情,只算作譯了一半。許淵沖的翻譯,可謂“信、達(dá)、雅”:WhenIlefthere,willowsshedtear。Icomebacknow,snowbendsthebough。因?yàn)橛⑽牡摹按沽笔莣eepingwillow(垂淚的楊柳),許譯說楊柳流淚,既寫了垂柳之景,又表達(dá)了依依不舍之情。大雪壓彎了樹枝,則既寫了雪景,又使人聯(lián)想到戰(zhàn)爭的勞苦壓彎了征人的腰肢。
有一個(gè)小故事,許先生多次提及。當(dāng)年奧巴馬提出醫(yī)保議案,民主黨贊成,共和黨反對,反對票超出5票。許先生在美國的兒子把許淵沖《江雪》譯文,以郵件的方式發(fā)給奧巴馬和一位共和黨參議員。“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孤舟蓑笠翁,獨(dú)釣寒江雪。”這位參議員本來反對醫(yī)保議案,讀完《江雪》之后,非常欣賞老翁清高獨(dú)立的精神,做出了獨(dú)立于黨派之外的選擇,改投贊成票,使得贊成票超出7票。為此,奧巴馬還專門寫信給許先生兒子表達(dá)感謝。這是中國古老文化穿越時(shí)空的魅力。
中國文化如何走出去?許淵沖認(rèn)為,關(guān)鍵是翻譯,翻譯正確,打破文化隔閡,能讓人看到我們真正好的東西。“翻譯不是只翻譯形式,而是要翻譯內(nèi)容。文學(xué)翻譯要變成翻譯文學(xué),因?yàn)榉g本身就是文學(xué)。”
“我一生向著求美的標(biāo)準(zhǔn)努力,是一個(gè)典型的‘享樂主義者’”
身處陋室,家徒四壁,過著簡樸的生活,整日伏案勞作,許淵沖卻說自己是一個(gè)“享樂主義者”。
西南聯(lián)大時(shí),旁聽馮友蘭的《中國哲學(xué)史》,許淵沖覺得自己的精神狀態(tài)已經(jīng)脫離了不自覺的“自然境界”,但又覺得“功利境界”和“道德境界”也不能說明自己的思想情況,就自擬了一個(gè)“興趣境界”,那就是自得其樂,興趣使然。至今,這種“興趣境界”依然是他的追求。
這種興趣,表現(xiàn)為一種旺盛的激情。許先生眼里,翻譯中“求美”的快樂,覓得佳句的快樂,是什么都不能取代的。當(dāng)年翻譯《毛澤東選集》時(shí),金岳霖譯到“吃一塹,長一智”,不知如何翻譯是好,錢鐘書脫口而出:Afallintothepit,againinyourwit。原文只有對仗,具有形美;譯文不但有對仗,還押韻,不僅有形美,還有音美,真是妙譯。錢先生化平常為神奇的睿智,讓許淵沖佩服終生,每言及此,津津樂道,嘆賞久之。后來他譯《毛澤東詩詞》譯到《西江月·井岡山》下半闋時(shí),就模仿錢先生譯法,用雙聲疊韻來表達(dá)詩詞的音美。
有人曾問許淵沖,如何看翻譯這個(gè)外人看似寂寞的事業(yè)?老先生回答說,翻譯是和作者的靈魂交流,怎么會(huì)感到寂寞呢?德國哲學(xué)家叔本華說過,美是最高級的善,創(chuàng)造美是最高級的樂趣。而翻譯工作就是創(chuàng)造美。孔子說過,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知之就是求真,這是客觀需要。好之就是求善,善既是客觀需要,又是主觀需求。樂之就是求美,是主觀需求。不求美并不會(huì)受到懲罰或傷害,但進(jìn)入了美的境界,無論是科學(xué)上、道德上還是藝術(shù)上,人都可以享受到一種精神上的樂趣。如論語中說的“發(fā)奮忘憂,不知老之將至”的孔子,或者簞食瓢飲、不改其樂的顏回,或“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fēng)乎舞,詠而歸”的曾皙,都是自得其樂的例子。“我一生向著求美的標(biāo)準(zhǔn)努力,是典型的享樂主義者,怎么會(huì)覺得痛苦呢?”
“一個(gè)人如果有一百句值得后世記住的句子就夠了。”96歲的許淵沖,一生理想是“用翻譯創(chuàng)造美”,且至今筆耕不輟,翻譯莎士比亞,常常到深夜3時(shí)。老先生笑曰:“天天和古人打交道,跟莎士比亞打交道,超越時(shí)空交流,樂何如哉?”

賬號(hào)+密碼登錄
手機(jī)+密碼登錄
還沒有賬號(hào)?
立即注冊